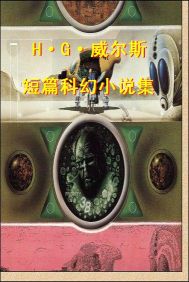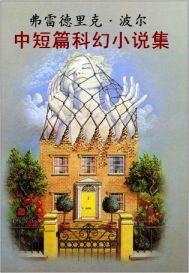217 科幻之路 第二卷-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对全国的宗教不利,则是没好处的。我想,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里,搞由政府赞助的研究工作,差不多也会遇到同样的种种困难。如同我所讲的那样,我碰到了一系列困难,不过这些困难只在一定程度上使我退缩了一下。例如,在单性生殖的研究方面,跟巴苔荣的无父青蛙相比,我已搞得更进一步;我还对爬行动物以及鸟类的蛋卵进行了单性生殖的人工引导;但到目前为止,在哺乳动物的单性生殖方面,我仍未取得成功。然而,我并没有放弃!”
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实验室,在这儿,到处都是畸形动物,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实验室是最最有趣的”,哈斯库姆告诉我说,“它的官方名称是‘物神院’。在这儿,我只是又一次利用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搞起了研究工作。这里的百姓对奇形怪状的动物真可谓是情有独钟,而且他们还通过最最怪诞的表现方式,用小型的陶土或象牙塑像来表示物神。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人工能否改进自然这一问题搞清楚的,我还开始对我所搞过的实验胚胎学进行回忆。但在这儿,我只使用了实验胚胎学中最最简单的方法,即利用发育最初阶段的可塑性,来制造双头巨兽。当然,双头巨型水螈和双头巨型鱼类的研制已在几年前由德国动物学家施培曼和史达卡尔两人分别搞过了;因而我只不过是运用福特先生的大规模生产原理来大量地制造这两种双头巨兽。不过,我也有我的特制品:三头蛇和长有一个冲天脑袋的双头蟾蜍。三头蛇的制造有点困难,但需求量很大,而且能卖好价格。双头蟾蜍的生产则简单多了,只要把哈里森的方法运用到小蝌蚪上面就行了。”
然后,哈斯库姆把我领到最后的一所房子里。与另外三所房子不同的是——在这儿,没有研究取得进展的任何迹象,里面空荡荡的。房间里挂着黑乎乎的窗帘,只从顶部透出些亮光;房子的中间是一排排的乌木长凳,长凳前面是个讲台,上面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球体。
“在这儿,我正着手搞强化心灵感应方面的研究,”他对我说,“关于这一研究的全部情况,将来你一定得抽空来看看,因为这确实很有趣。”
你可以想象出当时我那目瞪口呆的样子,因为这类奇事实在让我感到吃惊。每天我都要跟哈斯库姆进行交谈,慢慢地这种交谈成了我们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天,我问他是否已对逃跑不再抱希望了,他回答时支支吾吾的,很是怪异。最后,他对我说:“说句老实话,亲爱的琼斯,最近几年来我真的几乎没考虑过要逃跑。在最初看起来,要我故意放弃这个念头,并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转移到工作上,这是如此地不可思议,当时我几乎可以说是很愤怒。而如今,真的,我对我是否要逃跑已拿不定主意了。”
“不想逃跑!”我叫嚷道,“你不可能是指这个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他回答道,“我最最希望的就是在强化心灵感应方面取得进展。嗨,伙计,你可知道我得到了一个多好的机会啊!并且这项工作进展得如此迅速——我可以预见一切已快成功了。”他停了下来,沉默不语。
然而,尽管我对哈斯库姆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极感兴趣,我还是不想为了他那反常的求知欲望来牺牲我的前途。不过他是不会丢下他的工作的。
最最激发哈斯厍姆的想象力的买验是他在大众心灵感应方面进行的那些实验。在英国,在变态心理学说还不怎么流行的时候,他已完成了医学方面的学业,还幸运地结识了一个热中手搞催眠术研究的年轻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的介绍,认识了一些伟大的先驱,如布拉威尔、温菲尔德等人。结果是他自个也成了一名合格的催眠师,而且挚识相当渊博。
在遭监禁的最初那段日子里,哈斯库姆对圣舞开始感兴趣。那儿的人们在满月的每个晚上都要跳圣舞,认为这是向天庭赎罪。所有的舞蹈者都属于一个特殊的教派。他们跳着激动人心的舞蹈,这一系列的舞步象征着追逐、战争、爱情方面的种种活动。在跳完之后,首领把他们带到试验台上,然后进行施眠。这给哈斯库姆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就会身体靠着乌木栏杆向后倒,并处于沉沉的昏睡状态。这使他回想起法国科学家们所记录的那些关于集体催眠方面极其可怕的例子来。接着,首领从试验台的一端催眠到另一端,对每个人耳语一句简短的话语;然后,根据古老的礼节,他走近祭司王并大声说道:“尊敬的陛下,命令这些舞者去做你喜欢的事吧。”听到这句话,国王就会指示那帮人去做一个先前保密的动作。指示常常是去拿取某个物品,并放到假想的圣殿里;或是去迎战敌人;或是扮成某种动物或飞鸟(这是那帮舞者最愿意做的)。不管这指示是什么,被施了催眠术的人都会去执行,因为首领的耳语已成了一种命令,使他们只听到国王所说的话,并去执行。在他们奔跑的时候,可看到最最奇怪的景象:他们对路上的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只是在寻找着国王要求他们去拿取的葫芦或是绵羊之类的东西;或是用一种象征的手法朝着我们所看不见的敌人冲去;或是一下子匍匐在地,发出狮子般吼叫;或如斑马奔驰;或如鹤、鹭翩翩起舞。命令执行完毕之后,他们就如木头一般僵立着,直到首领向他们跑去,从一个身边跑到另一个身边,用手指在他们身上一点并大喊一声“醒来”为止。他们醒过来了,没精打采地,但是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已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跳回到那间独特的简陋小屋或是会所之类的房子里。
这种对催眠暗示的敏感性吸引了哈斯库姆,他获准可更近距离地对这帮舞者进行观察。他很快就证实了:这些人作为一个部落,极易分化离异,轻而易举地就能让他们进入一种沉沉的催眠状态;可是,虽然这种催眠状态下的潜意识完全不同于清醒状态下的潜意识,它还是包含了欧洲人在催眠状态下的潜意识所没有的部分特征。像大多数早期忙着搞心理学研究的人一样,哈斯库姆曾对心灵感应感兴趣;而现在,由他控制着这批催眠对象,他就对这个课题开始真正地进行研究。
通过挑选出两个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催眠;接着向其中一个发出暗示,再通过这人把暗示传送给一定距离之外的另一个人,而其间并没任何物质方面的中介作用——通过以上这一实验,哈斯库姆很快就证实了心灵感应的存在。后来,即在他工作的顶峰时期,他发现若同时向几个对象进行暗示,其心灵感应的效果要比一次只向一个人进行暗示时强得多——因为这些被施了催眠术的人正在进行相互强化。
“我在研究超意识,”哈斯库姆说道,“而且我已经获得了超意识的雏形。”
我得承认,对通过强化心灵感应的效果所展示的前景,我几乎跟哈斯库姆一样地高兴。
哈斯库姆认为,当所有的对象几乎处于同一种心理状态时,就会出现超常的强化效应。
无疑地,从理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一观点似乎是正确的:起先,要达到这种相似状态很难;然而,慢慢地我们发现,把催眠对象调到同一个音律是可能的,如果我可以这样比喻的话,接着有趣的事情就真正地开始出现了。
首先,我们发觉在越来越大的强化作用下,我们司以把心灵感应传到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最终我们能把命令从首都传送到几乎100英里之外的国界线。接着,我们还发现,对于那些实验对象来说,为了接受心灵感应的命令,没必要先进入催眠状态。几乎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性格稳定的人,都可以不经催眠就受到心灵感应的影响。然而,最最不同寻常的是那些起先我们称之为“近效应”的心灵感应,因为一直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近效应”名不符实,它有可能向远处传送。在哈斯库姆向一大群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对象暗示了某个简单的命令之后,如果径直在他们中间走动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极其异常的感觉,就如同感受到某个超人正在用威胁的语调,以铺天盖地之势重复着这一命令,一方面我们觉得必须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似乎只是命令的一部分,或者只是那威力比我们大得多的指挥力量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形容的话。而这种感觉,哈斯库姆声称,就是超意识的真正开端。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巴格勒。哈斯库姆的下意识里都是古藏族喇嘛教所用的祈祷轮。他提议说,最终他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催眠诱导,并接着向他们传送一段祷辞,从而保证所有的人每天都的的确确在做祷告,而且同时,这还无疑会大大加强祈祷的功效。因此,根据上面这个例子,在灾难或战争时期,利用心灵感应的增强效应使全民长时间地一起抗灾或作战,这将是件可能的事情。
巴格勒对此深感兴趣。他设想着,自己正通过这种精神工具随心所欲地向人们灌输这些思想。他还想象着;自己在发布命令,全国的人从催眠状态下醒过来,他们在执行命令……他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跟他的梦想相比,报业辛迪加老板、甚至是战争煽动家的那些美梦,都将黯然失色、自惭形秽。当然,他希望在具体方法上得到哈斯库姆的亲自指导;同样理所当然地,我们不可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虽然我得提一下,如果他什么时候打定主意不理哈斯库姆。开始自己搞实验的话,他可能会决定去干些什么?对此我常感到些许不安。这个原因连同我一直想离开此地的渴望,导致我再次试图找到一个逃跑的方法。接着,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可能就是这种精神方法(即心灵感应)本身导致了我们遭囚禁,而我对心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