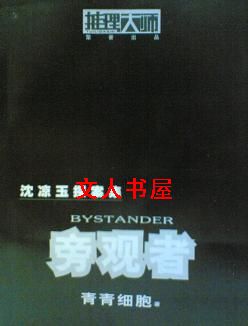投影 作者:[美] 凯文·吉尔福伊尔-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知道,”别人听到这话也许会笑,但他没有。“这就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有一天,他们可能要求你选择站在哪一边。当他们那样干时,我希望你选择自保。”
“才不会呢,”巴威克说。“我的职业生涯都是你给的。如果不是你安排我报道凶杀案,我可能到现在还在接听电话转录讣告呢。”
“在这件事上你就听我的话吧,保住你的工作,这是一份好报刊,我会在某地重新立足。不管在哪儿,只要你感兴趣,你都会有一份工作,不管是什么。也许你会走运,也许那是一个比这个城市有着更多变态杀人案的地方。”
“希望如此。”她神情黯淡地说道。
“那剩下来的那些混账事就跟你无关了。我不希望牵扯到你。这是一个命令,反正就这么着了。”
“一个命令。啊?”
“啊——嗯。”
“话又说回来了,也许到不了那个地步。”
“是啊,”他承认道。“事情是变化的。在一切尘埃落定以前,也许你就破了‘威克恶魔’那个案子,获得了普利策奖,让我脸上有光。”他这次也没有笑。
萨莉离开的时候没做任何承诺。马利克敲击着电脑键盘检索一堆邮件,都是当巴威克坐在他办公室时收到的。萨莉在新闻事业中可以担任很多角色,马利克心想,当个专栏作家或是编辑都可以。当她第一天来到《芝加哥论坛报》时,她说想要当一名记者是因为她喜欢拥有读者但又不想人太多。马利克听到她这番话不禁笑了。她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马利克想知道她在那个电脑游戏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第三章
在斯通大街的大房子里,戴维斯坐在前窗旁的大皮革椅上,读着一本平装版的书——《死亡时刻》,讲的是一个名叫修斯的杀人犯的故事,他的上诉都已经被驳回,行刑日期也已定下。就在午夜。他准确地知道自己将在几分几秒死去,但他承受不了知晓这一切带来的心理负担,于是通过一个囚犯花钱雇了另一个囚犯。他不知道那人的身份,但雇他在行刑前的任意一天把自己杀掉。这种死亡时间的不确定使修斯感到高兴——不再接受死亡的等待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他高兴得不再想死。所以,休斯开始试图躲避来自有限范围之内的刺杀。
这是一本无聊的书,但戴维斯却为它着迷,仅仅在几个小时内就读完了前两百页。这种天方夜谭似的小说——集科幻、惊悚、神秘于一身——曾是他十几岁时的特别爱好。那时,他每星期都要读上两三本这样的书,还总不忘随身带上一本,在闲暇时抽空翻开光亮的书皮并用一只手把书举到面前,从不浪费一分一秒。早餐时,公共汽车上,课间休息时,午餐时,在五金店打工的间隙,甚至骑自行车时他都在读。
随着年龄的增加,戴维斯为消遣而读的书越来越少,逐渐缩短的空闲时间被不同的困扰占据。在医学院时,他对用假蝇钓鱼一种垂钓方式,又称虫形毛钩钓法。着迷,他更多的是在公寓旁的公园中练习垂钓而不是去威斯康辛的溪流中。三十岁出头,戴维斯开始迷恋赛车——他用一张遗产支票还清了学生贷款并买了一辆小型宝马车——他把时间花费在赛车道上。随着安娜逐渐长大,杰姬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戴维斯把宝马卖了,开始投入到对家谱学的研究中。在那个无窗的蓝色房间中,他经常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潜心探究家族祖辈们的生死记录,试图通过了解祖辈认识自己。在寻找杀死安娜凶手的过程中,对家谱学的研究被他搁置一边,但由于害怕坐牢,他同样放弃了对杀人犯的搜寻。
每一次的沉迷都是消沉沮丧的特征——他现在明白了这点。快乐的人会时不时盼望一段时间的倦怠,但对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来说,无聊的时间是不能容忍的。不快乐的心里塞满了悔恨、内疚,以及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境,并且不能停止对最坏情况的设想。飞舞的渔杆、赛车的跑道和附有家庭历史的一张张名片充斥着戴维斯的大脑,为他驱散了不开心的想法和多余的顾虑。
自从和琼结婚以来,原来的压力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是他的念头中仍然存在可能发生灾祸的忧虑和下意识的畏惧感,不过只是作为紊乱无序、无法确信的空想罢了。蓝色房间中的档案箱里,旧一点的袋子里装的是跟他家庭有关的档案,稍新点的袋子里装的是关于安娜凶手的线索,已经尘封了四年多。琼曾提过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画室,以便在她退休后他们两人可以在这里一起画画。在戴维斯的生活中,现在比原来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所以他有时间享受闲适了。他珍惜这种没有限制,不用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时光。他终于可以坐在面向斯通大街的窗前,把以前四十年中没有时间阅读、情节可怕又引人入胜的书都通通读一遍。虽然对安娜的回忆一直围绕着他,但那已不再使他困扰。他也开始对自己被枪击一事感到释怀,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这事难道不是电视电影中才出现的。
门铃响了,但戴维斯不想应门。那也许是个可以留在门廊上的包裹快递,也许是一个他不愿参与签名,由邻居发起的请愿书;那也可能是上中学的孩子为了某个团体旅行而来卖糖果、蜡烛筹集资金。他并不反对团体旅行,但现在确实不想马上应门,他不想自己的闲适生活被打断。可是他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路过的人肯定会看见他的脑袋。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十多年,可不想被人认为是一个从不给别人开门的怪老头。于是他站起来,把书平放在茶几上。
这个男孩在六年的时间里长大不少,已不再像个小男孩了。他比戴维斯矮不到一只手的高度,长长的金色鬈发在他头上飞舞着,就像微风中随风旋转的中国风筝;皮肤上有一层细微的汗毛,胳膊上开始长肌肉了;他的手上有几条粉红色的疤痕,脖子上围了一条银色围巾;鼻子和嘴下面松散地留着一些将来某天会被刮掉的东西;脸被眼睛和发线突显出来,鼻子底部还有一个明显的红白色脓包;他穿着双色搭配的短袖衬衫,宽松的卡其裤和凉鞋——十几岁孩子惯有的随意装扮。
“穆尔医生。”他就说了这么多。
戴维斯活动了一下舌头下的分泌腺来对付嘴里的干燥,他想知道这次又是怎样一种小把戏。他想弄清楚像这样试图捉弄他的人是谁,希望他做什么。他需要知道答案,然后不让他们得逞。戴维斯扫了一眼男孩的身后,找寻他妈妈的踪影,并巡视街道上有没有她过去经常开的红色汽车。
“你想干什么,贾斯汀?你不应该在这儿。”他大声说道,万一附近有人,或是贾斯汀宽大的口袋里装了麦克风,这样他们才听得到。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贾斯汀回答,当他感觉到戴维斯的为难之后又补充道,“如果妈妈知道我在这儿,我会有大麻烦的。我逃了两节课。但我要说的事很重要。”
戴维斯知道自己正在犯错误,但他还是招呼孩子进屋,理由与所有犯错者的理由一样: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贾斯汀礼貌地停在过厅处,神情不太自在。他把重心压在右脚上,而用左脚的运动鞋在地板上画着半圆的形状。戴维斯请他进客厅并随他进去。这个男孩坐在沙发边上,膝盖紧贴着咖啡桌桌脚,就好像如果他的大腿后侧和沙发垫子挨在一起,垫子就会渗出黑色墨迹一样。戴维斯拉上了前面的窗帘。
“等一下,”他对贾斯汀说。戴维斯拿起另一个房间的无绳电话给琼打了过去。上次和她联系的时间是两点半,她说要在回家路上去杂货店逛一下。如果她知道贾斯汀在这个房间里,肯定会疯掉的。
“亲爱的,”他说,“你能不能顺便捎些陶土回来,还有你上个月买的那种香波?对,就是那个。对不起,我应该把它列入你的购物单上的。谢谢,我爱你。”这将在她的路途中增添两次停留。他猜想他们大概还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冒险到这里来肯定有要事,”戴维斯说,没有留意从和贾斯汀在门前说话到此时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妈妈告诉我了。”贾斯汀说道。他看上去有渴望的神情,并且如坐针毡,但戴维斯把这种紧张不安当做他这个年龄的特征:他变化的身体缺少慰藉,每天晚上,疼痛都会伴随着他的脚、胳膊和脊骨的生长,让他疲惫。但那不是紧张不安。事实上,来这里就是一种有信心的表现。这是一种挑战。贾斯汀的双眼大胆地挑衅着戴维斯。虽然未被邀请,但贾斯汀还是冒险在此出现,他希望戴维斯作为回报也能冒险做点什么。
戴维斯不知道自己会为冒险付出什么代价,所以他决定守口如瓶。“她告诉你什么了?”
“她告诉我,我是从哪儿来的。”
“是吗?”
“她说我是个克隆人。”
“是吗?”
“她告诉我,我是一个纽约州男孩的克隆人,他名叫艾利克·伦德奎斯特。”
“好的。”
“这是真的吗?”
戴维斯笑了笑:“我不能说。”
“你不再行医了。”贾斯汀说,他故意在“行医”这个词上顿了顿。戴维斯退缩了,突然想起火、丢失的宠物以及八年前琼就开始有的忧虑和内疚,那些回忆原本都在现在的快乐中蒸发掉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又害怕了,不是害怕如果被抓到违反了那个管制令会发生什么,而是害怕贾斯汀本身。他说不清楚那是为什么。“他们能对你做什么?”
“能做很多。”戴维斯没加过多的解释,“你妈妈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大约六个月前。”
戴维斯在他的脑中计算着。“让我猜一猜。你的生日?”贾斯汀点了点头。“他们总在生日时这样做。这肯定在某本书中或别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