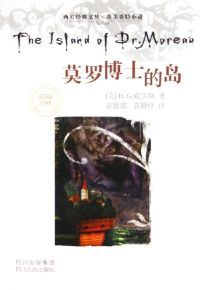熊熊燃烧的岛 作者:[苏联] 阿·卡赞采夫-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霹雳一声,惊天动地。四百俄里外,窗玻璃都被震裂。一千俄里外犹可听到隆隆的轰鸣之声。一个火车司机,在离出事地点八百俄里的坎斯克市附近,猛然刹车,他觉得似乎自己的列车有一节车厢爆炸了。
原始森林上空狂飙骤起,一片火海。帐篷、鹿儿在空中飘荡……飓风摧毁了游牧人的驻地,成片的树林连很拔起……”过去被称为埃文基人的屈古斯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距离爆炸地点二百五十俄里的地方,飓风掀去了屋顶,而在五百俄里以外,围墙都被飓风吹倒了。
遥远的城市里,餐具柜中的杯盘器皿叮当作响,壁钟停止了摆动。
伊尔库茨克、塔什干、梯弗里斯和耶拿(德国)的地震站都测出了这次震中位于中通古斯卡河地区的地壳震动。
伦敦的气压记录器测到爆炸气浪,这气浪绕地球两周。
整整三夜,不仅在西西伯利亚,而且在欧洲和非洲北部,天色都不转黑。通古斯爆炸的第二天,夤夜时分,当地的一位教师毫不怀疑夜里是否能拍摄照片,就带着照相机出发了。他在纳罗夫恰特、奔萨省拍的照片,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在巴黎、黑海和阿尔及尔也同样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白夜。
那几夜,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波尔卡诺夫正在西伯利亚。这位学者善于观察和准确地记录他的所见所闻。他在日记中记载:“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倾盆,但同时却又异常的明亮,亮得在露天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报刊上的小号铅字。当时没有月亮,然而乌云却被一种略带黄绿色的、有时转呈玫瑰色的光线照耀着。”
学者们发现,在八万六千米的高空有闪闪发光的银白色的云彩。
很多学者断定,有一颗空前未有、硕大无朋的陨石坠落在通古斯原始森林之中。
就在这令人难忘的一九○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早晨,四个安加拉原始森林地区的居民正沿着草木丛生、岗峦起伏的河岸拉纤。沿河丘岗险峻,如刀切般的陡峭。原始森林紧靠着河的两岸,远处河面上面薄薄蒙上一层紫罗兰色的轻雾。
走在前面的是流放犯巴科夫,约莫五十岁左右,体格魁梧,蓄着浓密而火红的大胡子,当他呼唤同伴或放声大笑时,沿河很远就可听到他那洪亮而浑厚的低音。
阴沉的当地居民喜爱听他这笑声,对他的坚毅和博学非常尊敬,并为他惋惜。他们知道巴科夫的心脏有病,他有时背靠着松树,张口吸气。
在原始森林里,按习惯不向外来人提这样的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到这儿来。从外表上看,巴科夫与当地其他居民没有什么区别。他那将头发围头剪去一图儿成刘海的发式、浓密蓬松的大胡子、一身破烂不堪的猎人的翻毛皮衣,脚上蹬着一双干瘪不平的破旧的亚细亚式的山羊皮半统皮靴,这种皮靴是按脚型制作的,因此不会磨出茧子来——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使人认出他来,譬如说,最近一届国际物理学家会议主席霍尔姆斯捷德先生,要是在这里,在这遥远的原始森林之中,也不能立刻认出他就是彼得堡的巴科夫教授。如果首都的医生们得知患心绞痛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这儿当纤夫的话,准会大吃一惊。
悬崖下,顺着纤绳往下,可以看到一条小船,这是条舷高头尖,用皮条缝连起来的西伯利亚古式小木船。前面,巨大的峭壁遮盖了半片天。一排排木筏从峭壁后顺水飘然而出。前边木筏上,木排工住的小木房旁聚着一群绵羊。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当地人,身穿蓝色衬衫,未系腰带,钻出小木房,举首望天,一边伸懒腰,一边不时地搔搔自己的背。他把嘴张得异乎寻常的大,打着阿欠,画着十字。
突然,一声极为可怕的爆炸。有个什么东西一闪,光亮耀眼,使人目眩……
那些向前弯着身子背纤的安加拉人,猛地栽倒在地。只有巴科夫一人攥住了一株树,站住了脚。
一个木排工跌得两膝着地,张大嘴巴。羊群咩咩哀叫,惊慌地往水中奔避。
紧接着是第二次爆炸。这次更为可怕……木排上的小木房被摧毁,在水中飘荡,周围水面上浮露着落水的绵羊的背脊。浪中还有件蓝色衬衫闪了一下……
空气稠浓沉浊,就地向巴科夫袭来。他的一只手被震脱,人从悬崖上飞落水中。
他浮上水面以后,看见河上的巨浪,犹如高耸的堤岸。巴科夫呛着水,用嘴呼吸空气……在精疲力竭时,他想:“卡佳,我亲爱的女儿,你在奥布霍夫斯基死于警察的枪弹之下,至少还有父亲为你悲痛万分,而我那在彼得堡的学生克列诺夫以后会不会记起我呢……?”
巴科夫眼看着已经空无一物的木排被折为两段,一根根木头被波涛打得向上撅起,竖在水中。
浪涛猛烈地冲击着巴科夫。
如果这位从前的彼得堡教授没有被纤绳缠住,如果那些安加拉人没有拖住纤绳把他从水中救出来,那么以后很多令人惊异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篝火烧得很旺。巴科夫的风雪大衣铺摊在木撅上烘烤着,安加拉人默不作声地坐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一对一地和熊搏斗,都能驾着一叶扁舟渡过急流险滩而毫无惧色,可是这样的事情他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人不怕神,不怕鬼,但这次把他们摔倒在地之后,他们驯服了——画十字祈祷了。
穿蓝衬衫的木排工也在篝火旁烘衣服;他出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绵羊而显得愁眉苦脸。
巴科夫背靠松树坐着。他心脏病的发作虽然已经过去,可是左臂还在隐隐作痛。然而巴科夫已经用那令人羡慕的男低音铿锵地说开了:
“让牧帅们用上帝的意旨来吓唬人吧!但你们,猎人们,只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双手。从天上陨落下来的石头是可以用肉眼看见和用手摸到的。人们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陨石。”
“这不是块什么小石头,老弟,今天这块大极啦。”一位白发仓仓、仪表令人起敬的安加拉人说道。
“对!”巴科夫同意道,“今天轰然而坠的是整整一座山岩,不比我们路旁的那个山岩小。不过这座坠落下的山岩大概是铁质的。”
“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岩石,”木排工说,“魔鬼我倒听说过。”
“坠落下来的是铁岩,”巴科夫满有把握地说,“虽很少,但是有。千载难逢啊。”
“那你见过吗?”
“这种陨落铁岩所遗留下的痕迹我见过。”
“老弟,你究竟在哪儿见过这种痕迹的?”
“在美洲,我曾去参加过一个代表大会。北美有一石漠荒原亚利桑那州。在这荒原里有一块地方叫‘鬼谷’……”
“我说过吧——是魔鬼。”木排工插嘴说。
“一千年以前,在那个荒原,从天空坠落下一座铁岩。我向印第安人买了这铁岩上的两块小碎片。我看过那里留下的坑。这坑成了一个道地的湖,宽一俄里还不止,而深则达一百俄丈!”
“哎哟!”一个年轻的猎人极为惊讶,他竭力想象这骇人听闻的坑有多大。
“那座陨落的岩石一碰到地球,没有用火药就爆炸了。”巴科夫继续说道,“岩石飞行的速度是步枪子弹速度的五十倍。岩石在飞行中的全部能量立刻转化为热能。”
“当然,”木排工说,“子弹一打到铁上——就会因热而熔化。不过,我想,这不是什么岩石,而是魔鬼。”
“你能去碰碰魔鬼头上的角吗?”巴科夫狡默地问。
“要是遇到鬼,我就碰碰他的角。”西伯利亚人回答。
“宽一俄里还不止的坑?”最年轻的猎人打了个唿哨说。显然,他直到现在才想象出这个坑有多大。“在原始森林里的这个坑会是个什么样的呢?很想去瞧瞧。”
“大概不会比亚利桑那州的坑小。”
木排工人仔细地瞧着巴科夫,沉默了很久。然后向他微微靠近些说:“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个很可爱的人,”他恭敬地说,“看来,你的心脏八成儿受不了这拉纤的活儿。干嘛你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帮我们啊?你就到我这儿来干这事儿吧!我和你坐小船去,不过你能为我设法弄到赔偿绵羊的保险费吗?”
巴科夫坐下了,甚至忘了自己的心脏不舒服。沿着中通古斯卡河顺流而下,经过原始森林中的出事地点,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啊?!
巴科夫是个能象青年人那样对什么东西都能入迷的人。这位教授一旦激情“爆发”,正如他往日的同事所形容他的那样,就如脱缰之马,再也收不住了。他会多少天日日夜夜地待在实验室里,有时得别人去硬拖他出来散散心。而一旦他烦闷起来,就能一连几个星期躺在沙发上,连办公桌都懒得靠近。
巴科夫挺直身子,几乎要比墩实的木排工高出一个头。
“我想办法给你搞,老兄!”巴科夫向他保证,“如果你能把我带到爆炸地点,如果你同意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个坑,我替你去想办法。”
“去看——你去看吧。老第,我在小船上等你,以免发生危险。”
巴科夫哈哈大笑。他拍着木排工的肩膀,催促自己的新伙伴动身。
木排工名叫耶戈尔·科瑟赫,他对这位流放犯的奔放性格惊诧不已,而且自己也被他这种遏止不住的热情所感染了。他立即吩咐自己的助手把打散的木排再收集到一起,并着手将木排上的一艘小木船配备好全部所需的物品。
一小时以后,巴科夫和科瑟赫告别了安加拉人,沿中通古斯卡河顺流而下了。
太阳已经下山。夜幕降临了。天空布满了乌云,开始稀稀落落地下起了雨,但天色始终不见转黑。他们乘风破浪,日夜兼程。
“不知为什么这么晚天还不黑。”西伯利亚人极为惊讶,因为他从来未见过白夜。
他俩停下来休息,可还是不见天黑。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