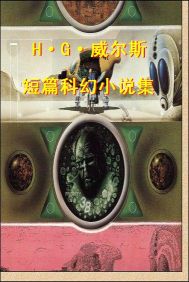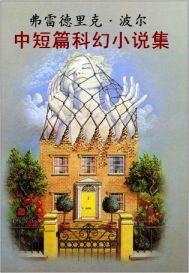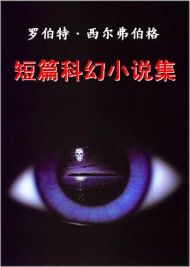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三辑)-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科奇斯这个角色。尽管我以前同戴特一起表演过,但想到要在观众面前表演完整个节目让我有些焦虑,但我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昙把戴特的燕尾服改小了一点儿,我穿起来漂亮多了,她又帮我在脸上画了印第安人的图案;当范站在我们独特的马戏场中央,通过麦克风赞美着我传说中的英勇,介绍我出场时,我大步走进充盈着黄色灯光的帐篷内,锯屑和兽粪(一只小兽在我们到达现场前曾到这里来吃草)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我高举着胳膊,挥动着系在短柄斧和飞刀上的飘带,享受着欢呼。整个七排座椅都爆满了,观众由景点工人、渔夫及其家人组成,其中还有少数旅行者(主要是徒步旅行者),还有一群肥胖的俄国女人,她们是由矮小的越南人蹬三轮车从距海滩很远的一家旅馆拉过来的。
观众们兴致正高,这要感谢刚刚表演的一场滑稽剧,昙扮演一个乡下女孩,川则演一个农村小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他的欲望通过一根伸缩杆反映出来,这根杆能弹出去十四英寸长,就系在松大裤子的胯部。
梅穿着一件坠满金属片的红色衣服,曲线被勾勒得玲珑有致,她以手脚伸展的姿势站在木板前,人们立刻安静下来。范坐在马戏场中央的一个木凳子上,切换了背景音乐,古老的詹姆斯·邦德电影主题曲。我向观众们展示着飞刀,转身瞄了木板一下,然后向梅掷出飞刀,将它结结实实地扎在她头上一英寸的木头上。
头四五下都完美极了,描画出了梅的头和肩膀。每一次飞刀扎入木板,观众们都发出惊叹之声。现在我无比自信地在转网躲闪中掷出一把把飞刀,配合着主题音乐装作躲避枪击,弯腰屈膝、收腹挺身、蹿蹦跳跃——可是一个疏忽,我大力快速掷出的飞刀离梅太近了,刺进了她手臂上方。她尖声大叫,从木板前捂着伤口蹒跚着躲开。片刻后她冷静下来,痛苦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从入口跑掉了。
观众们都吓晕了。范一下跳了起来,麦克风在他手中直晃。
有那么几秒钟,我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夸张的音乐如同一副栅栏将我全然隔离开来,当川关上音乐时,栅栏才轰然倒塌,我感到上千双眼睛盯在我身上。我无法抵挡这种注视,跟在梅身后逃进了夜色。
主帐篷立在沙丘顶上,从那里可以远眺海湾和蜿蜒的沙滩。这是一个温暖、多风的夜晚,当我从帐篷里跑出来时,长满蒿草的沙丘被一阵狂风吹过,扬起沙尘。
在我身后,范的大叫大嚷盖过了狂风呼啸和巨浪拍岸的声音,他在劝观众们留在座位上,节目马上继续。
月亮几乎是满月,但躲在云后,给云山镶嵌上了银边。我起初并没有找到梅,后来月亮穿破云雾,给黑色的水面铺上一条银光闪闪的道路,轻触着波光粼粼的层层浪花,映亮了沙子,我发现了梅——靠她红色的服装认出来的——还有另两个人出现在下面大约三十英尺远的海滩上;他们在照料她。
我从沙丘表面遛下去,滑进了松软的沙子,结果摔倒在地。当我拔出脚时,我看到昙奋力地顺斜坡向我跑来。她为保持平衡抓住了我燕尾服的领子,差一点儿让我再次跌倒,我们歪歪斜斜地撞在一起,彼此抓着对方才站稳。
她在衣服上套了一件尼龙夹克,这件夹克与梅的那件区别甚小——昙的这件绣有一只装饰着银星的蓝孔雀。她闪亮的头发垂在颈后,水晶耳环在耳垂上闪闪发亮,黑色双眸烁烁放光。她看上去就像是光组成的,这种幻象随着乌云重新遮住月亮而慢慢消散。不过最震撼我的并不是她的美貌。我总想弄明白她是如何表现出各种美的形态的,从清纯的女学生到性感女子,再到大家闺秀,现在这个闪亮的化身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仿佛这位世界女神恰恰只为这个时刻而存在……不,她的冷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它包围着我,穿透了我。甚至在她说话之前——她没有提及在梅身上发生了什么,仿佛那并不是可能致命的事故,不会破坏我的信心,让我一拿起飞刀就想退缩——甚至在我被她仿佛一切正常的冷静态度说服前,它就已经包围了我。
她说那只是常有的小问题,现在我们该回到帐篷中去,因为范快要没笑话可讲了。
当我们爬上沙丘顶时,我呢喃道,“梅……”
可昙截过话头,“那不过是擦伤。”她拉起我的胳膊,带着我向入口走去,步履轻快、从容。
我觉得像被施了催眠术——不是被诱人的声音或者来闻摆动的发光物体所催眠,而是是被一种流动的时间的脉动,一种宇宙的背景韵律所催眠。
我浑身充盈着异常的镇定,把自己与人群和劲爆的音乐隔绝开来。似乎我并没有在掷飞刀,而只是把它们放在适合它们的位置,旋转、猛地把它们弹出去,然后砰的一声,它扎中了木板,形成一个钢刀围成的人形,只比置身其中的那个柔软的褐色肉体和其孔雀蓝绸衣稍大一点儿。
戴特也从未得到如此的欢呼——我想人们相信梅的受伤是已设计好增加悬念的恶作剧;当昙和我深鞠一躬,然后一起走出大门时,他们的欢呼长久不息。刚一退到外面,她就贴向我,吻了我的脸颊,并说她一会儿再和我见面。然后她离开我向帐篷后方走去,赶最后一个节目。
通常这时候我该去帮帮少校,可是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这种心情。现在少了昙令人宽慰的影响力,我仍对伤害到梅难以释怀。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上沙丘顶。最后走到一条长满蒿草的水沟。我坐在草地中,望着蜿蜒的海滩。
沙地向北延伸了十五米远,然后地势从这里开始向上,成了一座布满植被的矮山。大树半遮着一排有斜坡瓦顶和开放门廊的小屋,它们距海很近,从窗中溢出的如瀑布般的黄色灯光照亮了下方的碧波。高悬在空中的月亮失去了银色的光辉,像是一块掺杂有熏黑斑点的骨灰瓷,月光下的成排椰树就像守卫着河道的嵌有利齿的城堡,掩映其中的是来观看我们演出的旅行者所住的旅馆。我能认出在它前面照得很亮的月牙形沙滩上来来回回的蚂蚁般的人影,听到微风送来的断断续续的音乐。远处,水面有如墨染。
我的思绪没有转到有关梅的事故上去,而是想着与昙的合作表演。动作飞快地闪过,急速的飞刀和灯光,我现在仍能回忆起那些细节:两指间金属的凉意,舞台边焦虑的范,翻着跟头扎在昙两腿问空隙的短柄斧刃上映着的火光。不过,最重要的记忆是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像是在发射指令,精心安排着我的行动,它们是那么有说服力,甚至令我觉得就算我的准头有误她也能够偏转刀锋。凭我对她的感情投入,我绝对相信——即便我们从未讨论过——我们未来会在一起,而且我相信她拥有能控制我的力量。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不过略微有些讨厌,我们无法平起平坐的想法打击了我,如果只由她来控制我们关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关系不会长久的。可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我的思绪便松弛下来,陷入了沮丧之中。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长时间,这时昙沿着海滩走来了,拨开了被风吹到脸上的头发。她身穿一件男式短袖衬衫,一条宽松闲适的短裤,带着一块毯子。我借助草地躲着她,挤在地上的一个缝隙内,虽不太舒服但可让我容身了,我等她走过这片草地。可她却停了下来,喊着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性地答应了。
昙发现我后止住了脚步,来到我的身边,她说,“你跑得太远了,我都没把握能找到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埋怨的意思,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昙在沙地上铺开毯子,拉着我坐下来。风开始一阵阵地从水面上吹来,她打起了哆嗦。
我问她是否愿意披上我的礼服夹克。
她说,“不。”接着双唇紧闭,突然从我身上移开目光,侧身转向一旁。
我以为自己一定是做了什么令她困扰的事,这令我忐忑不安,没有马上注意到她正在解开衬衫。
她脱掉衣服,很快把它团成一团,然后放在一边。她扭头与我对视。
我本以为平日里她的那种镇定恢复了——我几乎能看出她镇定自若——可接着我意识到她的这种冷静并不是她所独有的,而是我们共有的,是一种我们彼此信任的产物。在主帐篷里发生的事并不足她控制我,把我从惊惶失措中拯救出来,而是将我们的力量结合起来,驱除了恐惧。就像现在一样。
我吻着她的嘴及她娇嫩的乳房,狂喜于上面的汗所带来的略咸的味道。然后我拉着她躺在毯子上,进入了她的体内,尽管还很笨拙,且带有刹那的不安,但不知为何既狂野又纯洁,这是两年来的渴望和未言约定的自然高潮。后来,我们彼此挤压,如胶似漆,不断进发出激情,温暖火热的身体低语着古老然而决不缺少新奇的悄悄话和誓言,诉说着长久以来未说出口的事情。我内心决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这不是种抽象的想法,不单单是男人面对新的责任产生的本能反应,我不否认我也有使用暴力的念头——性爱与暴力来自同一个源头——但这是经过了仔细的考虑后得出的结果,我必须战胜种种考验,必须为了保证她的安全而流血,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会为了夺取利益而犯下杀妻罪行的,也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弑父。
破晓时分,云层又闭合起来,河面风息浪静。偶尔会有一丝微弱阳光刺透阴霾,把水面映得闪闪发亮,如同一大片刚刚刷上灰漆的天空。
我们爬上沙丘顶,拥抱着坐在一起,不想回马戏团去,不想破坏对昨晚长久的回味。没有生气的草地、没有活力的海水和死气沉沉的天空,给人一种时间本身已然静止的错觉。旅馆前的海滩上还堆满了被人丢弃的垃圾碎片。
你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