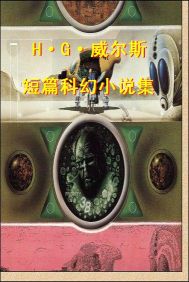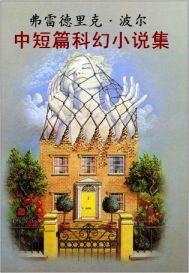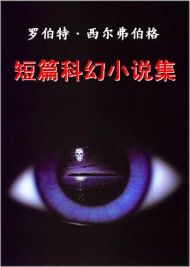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三辑)-第1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伤着了吗?”我问。我有点担心,也许我们不得不启动红色按钮来营救他了,那样的话,这次登山计划就毁了。
卡纳卡拉德斯摇摇头,动作很缓慢,不像是说不,像在检查身体状况。看着那些动作,我们觉得自己身上都疼起来:他的大脑袋和微笑的鸟喙前后向每一面旋转了差不多二百七十度,不易弯曲的前臂居然不可思议地弯了弯,长长的、分得很开的手指小心地拍打着脊背。
咔嗒,咝咝声,咔嗒——“我没事。”
“攀登下面的岩石带时,保罗会更小心的。”
“那就好。”
保罗的确很小心。但是岩石已经风化,还是弄出了几次山崩,但都没有直接砸着谁。十分钟后,大约爬了六七十英寸,他来到了山脊,发现一个很好的可以固定绳索的地方,叫我们上去。加里跟了上去。此人最讨厌别人踩松的石头砸在他身上,所以仍旧怒气冲冲。我让卡纳卡拉德斯跟在他身后,与他相隔三十英寸。虫子攀冰的技巧严格依照书本,动作不好看但很快。我最后一个爬上来。我尽量跟紧些,因为大家在到达岩石带之前的攀爬过程中会使巨石变得有些松动,隔近点我能看得清楚些,以免被它们砸到。
全体登上东北山脊。这时,这里的能见度几乎为零,气温骤然下降了五十度左右。大雪厚厚的,很柔软,但却暗藏危险。在乔戈里峰东面和眼前这个山坡上,也许就在身前,或是身后浓雾里的某处,我们看不见但却能听见轰隆隆的雪崩声。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我们保持着结组攀登的方式。
“欢迎到乔戈里峰来。”加里站在前面朝我们吼叫着。他的风雪衣、头盔、遮风镜以及下巴全结了冰,模样挺吓人,被横飞的大雪弄成了模模糊糊的一团。
“谢谢。”卡发出咔嗒嘶嘶声,我觉得语气显得颇为严肃庄重。“能来这里,荣幸之至。”
三号营地,刀刃般的Z形山脊起始处,山脊的冰柱下海拔23,200英尺
困了整整三天三夜,第四个夜晚也终于来临,我们无所事事地蹲在帐篷里,吃着营养块,还煮了一锅汤——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必定程序。为了把雪融化成水,我们用光了火炉里的热能。海拔高,又缺少运动,人人变得很虚弱。
整整三天,狂风怒吼,风暴愈发猛烈。如果把在二号营地那天一块算上,应该是四天了。
加里和保罗昨天出去了,由保罗领头,攀上陡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山脊。他们想在风暴中强行横穿陡峭的山崖,打算现在就使用固定绳,即便到登顶时固定绳不够用了也在所不惜。但是他们失败了。三小时后,在咆哮的风暴声中,他们回到营地,身上结了一层冰壳,几乎都被冻伤了。尽管保罗穿着先进的调温衣,但还是等了四个多小时才停止颤抖。
不管天气如何,有风暴也好,没风暴也好,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横穿这座山脊,那就用不着担心预留什么装备和食物来攻顶了。因为那样一来,根本就不会再有攻顶的可能。
我甚至不大确信两天前我们是怎么从二号营地攀登到这里来的,还开辟出了这样一块窄窄的地方。我们的虫子尽管多出几只腿,力气比我们大得多,但他显然也黔驴技穷了。我们决定最后几小时里采用结组攀登的方式,以防虫子坠下悬崖。按下红色报警键并告诉联合国的人——卡纳卡拉德斯倒栽葱摔进了五千英尺的嘎文·奥斯腾冰川——这样做可不太好玩。
“外星发言人先生,我们弄丢了您的孩子。但是也许您能刮掉他身上的冰,再克隆一个什么的。”不,不,我们可不想说这样的话。
结果便是,天黑后我们还在工作,头灯闪耀着,绳子钩在安全带上。为了不被狂风卷走落入漆黑的深谷,我们只好用冰锥把绳子系在山脊上。我们用冰镐挖出一个足以搭帐篷的平台。这里的空间只够搭一个帐篷群,把几顶小帐篷并在一起。帐篷离悬崖不到十英尺远,离雪崩路线只有四十英尺远,头顶上还倒挂着一个三层楼房那么大的冰柱。冰柱随时可能砸下来卷走人和帐篷。在这种地方待上十分钟都危险,更别提在高海拔飓风里待上三天三夜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其他地方不是如刀刃般的山脊,就是斜坡——雪崩的必经之地。
我可不愿身处此境,但总算有时间可以交谈了。
我们把帐篷连在一起,呈扁平的十字架形。中心部分极小,约两平方英尺,我们就在这个公共场所里煮汤、交谈。其余的空间也不大,仅够我们放下睡袋,然后大家蜷成一团,各自缩进自己的睡袋里睡觉。
在倒悬的冰柱下我们砍出的平台不够大,也不平稳。我睡在一个下坡处,头比脚高。这个角度说平也平,说陡也陡。平得能让我打打瞌睡,但又陡得让我时不时猛然惊起,懵懵懂懂以为自己正滑向深渊,忙不迭伸手抓冰镐。其实我的冰镐不在手边,而是和其他冰镐一起插在雪和坚硬的冰上,镐把上缠有蛛丝绳,和帐篷系在一起。为了固定帐篷,冰镐上的蛛丝绳足有一百英尺长,兜兜转转,绕着帐篷缠了几圈。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冰架上住稳当,还多用了十二个起固定作用的冰锥。
其实这样做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冰柱真的塌下来,如果山脊移动,如果狂风执意要卷走所有的绳子、冰镐和冰锥并吹翻帐篷,那我们和虫子就都得从山顶上滚下去。
当然,我们睡觉的时间很充裕。保罗带了一本平装书和一些杂志,这本书里有约十二个故事。我们偶尔传阅书和杂志,连卡也和我们一起轮流阅读。
第一天,我们谈得不多。在狂风的咆哮声里,在冰雹样的雪粒猛烈拍打帐篷的噼里啪啦声里,大家说话都很费劲,得尽量提高音量。最后我们连睡觉都厌倦了,只好试着交谈。第一天谈论的话题大多是登山和登山技巧:回顾我们的登山路线,列举出我们一旦过了Z形山,上到金字塔峰顶底部的雪丘就直接冲顶的利与弊。加里主张不管怎么样都直接冲顶,完成攀登,保罗却力主谨慎行事,他提议横向攀登到阿布鲁齐山脊,因为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攀登过了。卡纳卡拉德斯和我在一边听着。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开始询问虫子一些有关个人的问题。
暴风雪的第二个下午。“这么说你来自亚尔德巴朗星系①,”保罗问道,“你到地球来花了多长时间?”
【①金牛座上最亮的毕宿五。】
“五百年。”我们的虫子回答。他的四肢太长了,为了在帐篷里坐得不至于那么别扭,每一个肢体都至少折了两折。我想那样一定很不舒服。
加里“嘘”了一声,他从未关心过媒体对螳螂的报道:“你有那么老吗,卡?五百岁了?”
卡纳卡拉德斯轻轻吹了声口哨,我猜他这种动作相当于人类的微笑。“我出生在飞船上。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都是。我们的生命周期和你们差不多长。我们的飞船是……按你们的说法,世代飞船。”外面的大风愈发猛烈,吼声越来越大,他顿了顿,等风声稍稍减弱,又继续道,“来到地球前,我只知道飞船是我的家。”
保罗和我互相瞥了一眼。轮到我审问我们这个小俘虏了:他的国家,他的家庭,他们的国务卿。
“那么为什么你们……聆听者……不远万里来到地球呢?”我很好奇。虫子已经在好些场合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但答复总是一样,而且没什么意义。
“因为你们在这里。”虫子说。又是老调重弹。不过,我想这回答蛮讨人喜欢的。我们人类不是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吗?但他的回答仍旧一点意义也没有。
“为什么你们要花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不远万里来见我们呢?”保罗问。
“帮助你们学会聆听。”
“聆听什么?”我说,“你们?螳螂?我们倒是很有兴趣去聆听、去学习。你们说的话我们很乐意聆听。”
卡纳卡拉德斯摇摇笨重的脑袋。近距离看着螳螂,我才意识到他的脑袋与其说像虫子,不如说像蜥蜴类——恐龙或鸟的头“不是聆听我们,”咔嗒、咝咝,“而是聆听你们自己世界的歌声。”
“我们自己世界的歌声?”加里问得很唐突,“你是说,更加欣赏生活?放慢脚步,闻闻花香?诸如此类的?”加里的第二任妻子沉湎于玄想,我想这也正是他和她离婚的原因。
“不。”卡说,“我是说聆听你们的世界之歌。你们献身海洋,献身世界,却不去聆听。”
听得我头晕脑涨。我提出的问题把水搅得更浑了。“献身海洋,献身世界?”
一阵狂风吹过,整个帐篷发出嘎嘎扎扎的声音。风势渐渐减弱后我接着问:“我们没有啊,我们是怎么献身的?”
“死亡啊,杰克。”虫子回答,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死去以后就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
“可死亡与听到世界的歌声又扯得上什么关系?”保罗不解。
卡纳卡拉德斯的眼睛又圆又黑。在手电筒的灯光下,他注视着我们,但眼神一点也不咄咄逼人。“如果你死了,就听不见歌声了。”他连嘘带咔嗒一阵,“数百万年以来,你们这个种族的原子和分子一直与这个世界交流、循环。如果不是这样,这里也就不会有这支歌了。”
“你在这里能听见这支歌吗?”我问,“我是说在地球上。”
“不能。”虫子回答。
我决定换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你们给了我们CMG技术,”我说,“带来了许多美妙的变化。”胡说八道,我心里暗想。我更喜欢汽车还不能飞翔以前的世界,就算堵车也只堵在二维平面上,不会天上地下堵个满满当当。“但我们有点……嗯……好奇,你们什么时候才肯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秘密呢?”
“我们没有秘密。”卡纳卡拉德斯说,“在我们来到地球之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