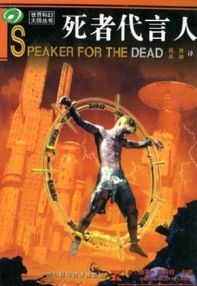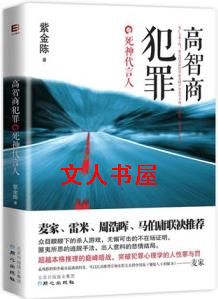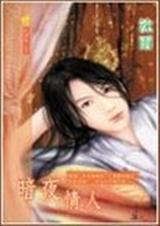死者代言人 作者:[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校看样子不错,教育水准很高。
参观结束后天已经黑了,塞费罗领着他重新同到修会,来到他和他的妻子——也就是阿纳多娜——的小房间。
堂娜·克里斯蒂在房间里,正通过放在两张床之间的终端指导学生作语法练习。
安德和克里斯托耐心等着,直到她结束工作才跟她打招呼。
塞费罗介绍了安德鲁后道:“他好像不太喜欢称呼我堂·克里斯托。”
“主教也一样。”他妻子说,“我的会名是Detestaio Pecadoe Fazeio Direito。”安德在心中翻译,憎恨罪孽,行为正直。
“我丈夫的名字简称起来挺可爱:Amai,阿迈,意思是‘爱你’。可我呢,对朋友大喝一声:oi!Detestai!你能想像吗?”
三个人都笑了。
“爱与憎恨,这就是我们俩,丈夫和妻子。你打算怎么称呼我?如果克里斯蒂这个名字你觉得太神圣的话。”
安德望着她的脸。这张脸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一个比他尖刻的人或许会觉得她是个老太婆,但她的笑容很美,眼睛里生气勃勃。让人觉得她比实际岁数年轻得多,其至比安德还要年轻。
“我本想直接管你叫Beleza①,但你丈夫恐怕会觉得我不规矩。”
“才不呢。他会叫我Beladona②。你瞧,一点点变化就把美人变成了毒药,真可气。你说呢,堂·克里斯托?”
【①葡萄牙语:美人。】
【②葡萄牙语:颠茄。】
“让你保持谦卑是我的职责。”
“而我的职责就是让你保持贞洁。”
安德不由自主地望望那两张分开的床。
“哈,又一个对我们禁欲式的婚姻生活产生兴趣的人。”塞费罗道。
“这倒不是。”安德说,“可我记得圣安吉罗鼓励夫妇共享一张婚床。”
“要这样做,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阿纳多娜道,“一个晚上睡,另一个白天睡。”
“安吉罗的教导应该遵守,但修会教友们也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塞费罗解释道,“我相信,有些老友能做到夫妻同眠,同时节制自己的欲望。但我妻子还很漂亮,我的欲望又太强了一点。”
“这正是圣安吉罗的用意所在。他说,婚床是考验我们对真理的爱的地方。他希望修会的每一位男女教友都能繁殖后代,同时传续知识。”
“如果我们那么做,”塞费罗道,“我们就只好离开修会了。”
“这个道理我们敬爱的圣安吉罗没弄明白,因为他那个时代里修会还没有成型。”阿纳多娜说,“修会就是我们的家,离开它就像离婚一样痛苦。一旦扎下根来,你就不可能随随便便再拔起植物。所以我们只好分开睡,继续留在我们心爱的修会中。我们觉得这样挺好。”
她是那么满足。安德忽然觉得自己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上双眼。她发现了,有点发窘,转开了视线。“请别为我们难过,代言人安德鲁,我们的幸福远远超过痛苦。”
“你误会了。”安德说,“我的眼泪不是因为同情而流,而是被你们的美好生活感动了。”
“不会吧。”塞费罗道,“连独身禁欲的神父们都觉得我们婚姻中的节欲是……说得好听点,古怪的。”
“我不这么想。”安德说。一时间,他想告诉他们自己和华伦蒂的友谊,像夫妻一样持久、亲密,却又像兄妹一样纯洁无瑕。可一想到她,他突然说不出话来。他在塞费罗床I二坐下,脸埋在手掌中。
“你怎么了?”阿纳多娜关切地问道。塞费罗的手轻轻搭在他肩上。
安德抬起头来,尽力摆脱对华伦蒂的思念。“恐怕这趟旅行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告别了多年来和我一块儿旅行的姐姐,她在雷克雅未克结婚成家了。对我来说才离开她一个多星期,可我真太想她了。看了你们俩——”
“你是说你一直独身,没有成家?”塞费罗轻声问道。
“现在又成了鳏夫。”
安德并不觉得用这个词有什么不妥当之处。
简在他耳中悄声道:“这样做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安德?我承认这一招对我来说太深奥了些。”
当然,这根本不是任何计划的一部分。安德有点吃惊:自己现在竟如此容易丧失自我控制能力。昨晚在希贝拉家里,他是别人的主心骨,而今天,面对这两位教友,他的表现就像昨晚的科尤拉和格雷戈。
“你到这里来是想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塞费罗道,“但是我看,你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比你自己知道的更多。”
“你一定觉得非常孤独。”阿纳多娜道,“你姐姐已经找到了归宿,你一定也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宿,是这样吗?”
“我不这么想。”安德道,“恐怕我太滥用你们的友善之心了,像你们这样没有神职的教友没有听取别人忏悔的义务。”
阿纳多娜爽朗地笑起来,“这个嘛,随便哪个天主教徒都可以听取异教徒的忏悔。”
塞费罗却没有笑。“安德鲁代言人,你对我们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显然超出r你来之前的计划。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现在我也相信,你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主教怕你,老实说我过去对你也心存疑虑。但现在不同了。我会尽我的努力帮助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破坏我们这个小村子,至少不会有意破坏。”
“啊。”简悄声道,“这下子我总算明白了。这一手玩得真漂亮,安德。你比我想像的还棒。”
这个促狭鬼弄得安德感到自己成了个玩世不恭的骗子手,于是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他抬起手,用指甲一拨宝石状微型电脑上那个小小的开关销,关掉了电脑。宝石不作声了,简再也不能在他耳朵里嘀嘀咕咕,也不能通过他的眼睛看,通过他的耳朵听了。 “咱们上外边走走吧。”安德说。
植人式电脑许多人都知道,所以他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们把这个举动看作他希望和他们私下里认真谈谈的表示,两人都很高兴。 其实安德的意思只是暂时关掉电脑,省得简老是开他的玩笑,但塞费罗和阿纳多娜却由于l电脑关机放松了许多,这样一来,他反倒不好再打开电脑了,至少这会儿不行。
走在夜色下的山坡上,和阿纳多娜与塞费罗谈谈说说,安德忘了简已经不能再听了。他们对他谈起娜温妮阿孤独的童年,后来有了皮波父亲一般的照料和利波的友谊,她又是如何恢复了生机。“但自从利波去世的那一晚,对我们来说,她好像也成了死人。”
娜温妮阿不知道大家是多么替她担心。在主教的会泌室,在修会老师们中间,在市长办公室,大家一次又一次讨论着她的不幸遭遇。这种待遇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他孩子也不是加斯托和西达的女儿,也不是这颗行星上惟一一个外星生物学家。
“她变得非常冷漠,只关心工作,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和其他人只有一个话题:如何修改本土植物的基因,使之能为人类所用;如何使地球植物在这里存活下去。问她这方面的问题她都乐于回答,态度也很好。但其他的……对我们来说她已经死去了。她没有朋友。我们甚至向利波——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打听过她,他说过去她把他当成朋友,可现在,他连其他人都不如,其他人至少还能得到她那种空空洞洞的和气态度。而他只要一问她什么,她立即大发脾气,完全拒绝回答。”
塞费罗摘下一片当地的草叶,舔了舔叶片背阴的一面。“你试试这个,代言人。它的味道很有意思。不用担心,对身体没什么危害,它的任何成分都无法进入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
“你最好还是提醒提醒他,叶片边缘锋利得像剃刀,小心划破嘴唇和舌头。”
“我正想说呢。”
安德笑着摘下一片草叶尝了尝。酸酸的,像肉桂,又有点像柑橘,还有点像口腔里的臭气。这种滋味像许多种东西混合在一起,没有一种好闻的。但气味十分浓烈,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人的地方。“这玩意儿能让人上瘾的。”
“我丈夫是要拿它打个比方,代言人,小心了。”
塞费罗不好意思地笑了。“圣安吉罗不是这样教导过我们吗?耶稣教诲世人的方法就是比喻,用人们知道的东西形容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草的味道确实很怪。”安德说,“但这跟娜温妮阿有什么关系?”
“这种比喻有点牵强。但我觉得,娜温妮阿在生活中品尝到了一种非常让人不愉快的东西,但那种东西的味道实在太重,它征服了她,让她割舍不下它的滋味。”
“你说的那种东西,是什么?”
“我给你说点玄而又玄的神学理论吧。我说的东西就是从负罪感中产生的骄傲。这是一种虚荣,一种自大。某一件过错,罪责本不在她,但她却担起了这个罪名。她觉得万事万物都以她为中心,其他人的痛苦也是对她的罪孽的惩罚。”
“她为了皮波的死责备自己。”阿拉多娜道。
“她不是个没头脑的傻瓜。”安德说,“她知道杀害皮波的是猪仔,她也知道皮波是一个人去的,与她无关。怎么会觉得是她的过错?”
“这种念头刚产生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个理由来反驳自己。后来我又看了皮波死的那晚的记录和资料。一切都很正常,只有一个暗示:是利波的一句话。他要娜温妮阿把皮波去找猪仔前和她一块儿研究的内容给他看,而她说不。就这些,这时别人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们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至少没在时刻有仪器记录的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里谈起这个话题。
“代言人,这句话让我们不禁猜想:皮波死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阿纳多娜道,“皮波为什么急匆匆跑出去?难道这两人为什么事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