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西马克中短篇科幻作品集-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会知道的,”兰德说,“这些我从未想过。”
“一个经常思考的人,”斯德灵说,“他在赶路时做了许多梦。因为没别的事情可干。他梦到了些傻东西: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傻的事情,但很难说它们不能实现。这种事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有时,”兰德说。
“有件事情我常想。一个傻到家的念头。之所以想它或许是因为我赶了太多的路。有时有人捎我一程,但通常是自己走。然后我开始想,假若一个人走得够远,他是否能把一切都甩到身后?他走得越远,他就离这一切越远。”
“你要去哪儿?”兰德问他。
“没有特别的目的地。只是不停地走,就这样。个把月后我会往南去。为冬天准备个好开头。北方这几州冬天来了可不是呆的地方。”
“还剩两个鸡蛋,”兰德说,“要吗?”
“天哪,伙计,我不行了。我已经……”
“三个鸡蛋没那么多。我可以另外弄些的。”
“好吧,如果你确定你不介意的话。要我说——咱们分了它们,你一个,我一个。”
蹒跚的老妇剪完花束,进屋里去了。从街头传来手杖的敲击声——兰德的另一位老邻居,晚上出来散他的步了。西沉的太阳将一抹余晖洒向大地。树叶是金色和红色,以及棕色和黄色的——自从兰德来的那天起它们就一直那样。而草则带着茶色——它们还未枯死,只是已穿上死亡的殓衣。
老人小心又吃力地走在人行道上,他的手杖探到了一块绊脚石,从而帮助他绕过它以免真得需要什么帮助(指摔倒)。他走得慢,就是这样。他在通往门廊的人行道处停下了。“下午好,”他说。
“下午好,”兰德答道,“你有个散步的好天气。”
老人客气地赞同了他的评价,还带点谦虚,仿佛他,他自己,也为这天气的好作出了些许贡献似的。“看起来,”他说,“似乎明天也会有个好天气。”而说完这,他就继续沿街走下去了。
这是例行仪式。同样的话每天都说。此情此景,就象这个村子和这样的天气,从未变过。他可以在门廊这里坐一千年,兰德对自己说,而老人会继续走过并且每次都是这同样的话说出口——一套固定情节,一段电影胶片放了再放。这里的时间出了问题。一年定格在了秋天。
对此兰德不懂,他也没有试图去弄懂它。没有让他尝试的方法。斯德灵说过,人的聪明可能超出了他们史前式的脆弱心智——或者,也许,是他们史前式的野蛮心智。而在这里,弄懂的可能性比原来在那另一个世界的更小。
他发现自己在用相似的、充满神秘的方式思考那个世界,如他思考这个世界一样。那一个现在似乎像另一个一样不真实。那么他还能否,兰德想知道,重寻真相呢?他又想不想找到真相呢?
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真相,他知道。进屋去拿出他床头柜抽屉里的那些相片,看看它们。刷新他的记忆,再次直面真实。因为这些相片,尽管也许可怕,却是种比他坐着的这个世界,或他曾经所知的那个世界更为鲜明的真实。因为它们不是人眼所见,也非人脑所出。
它们就是,真实。照相机摄其所见,不会说谎;它不编造,不推论,也不会记错,这比所谓的人脑要强。
他回照相馆——他把胶卷留在那儿了——店员从柜台后的盒子里拣出那个信封。
“一共是三美元九十五美分。”他说。
兰德从他的钱夹里取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把它放在柜台上。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店员说,“您是在哪儿照的这些照片?”
“是特技摄影。”兰德说。
店员摇了摇他的脑袋。“如果它们是的话,那它们是我见到的最棒的。”
“你想作什么?”兰德问。
男人把照片从信封里抖落出来,在中间挑拣着。
“这张,”他说。
兰德平静地看着他,“这张怎么了?”他问。
“这些人,有几个我认识。前面的这个,那是鲍伯?詹楚。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一定是弄错了。”兰德冷冷地说。
他把相片从店员指间拿走,把它们装回信封里。
店员找了钱。当兰德离开店铺时,他仍在摇头迷惑着,或许还有点害怕。
他小心地开车,但一点没浪费时间,穿越城市又过了桥。当到达河岸边的旷地时,他加了速,紧盯着后视镜。那个店员被惹恼了,或许会恼火到去报警。别的人见了这些照片也会恼火的。然而他对自己说,担心警察是愚蠢的。他拍这些照片既没有违规,也没有犯法。他有十足的权力去拍它们。
过了河又沿公路开了二十分钟,他拐入一条狭窄多灰的乡村公路并一直开下去,直到他找到停靠地,那里公路在接近一座横跨小河的桥梁处拓宽了。有迹象表明这个停靠点常被使用,一定是钓鱼者,在他们碰运气时把车停在这里。但现在这个位子是空的。
当他从口袋里抽出信封并抖落出照片时,他恼火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
而它就在那儿——尽管他已经记不起它的样子了。
他很惊讶,他居然拍了有手头这么多的照片。其中的一半那么多他都不记得曾拍过。但它们就在那儿,在他观看它们时,他的记忆,又复苏了,并且被增强了,尽管这些照片更比他的记忆鲜明得多。那个世界,他回想起来,就他的双眼所见来说,是朦胧又模糊的;在照片里它显得清晰而冷酷无情。焦黑的树桩立着,突兀又孤单,有些照片上的印像无疑是座被炸城市的实景。悬崖的照片则显示着不再有绿荫覆盖的光秃秃的岩石,唯有或近或远处有几截残桩,因为巧合的奇迹,还没有完全被火焰的狂浪所吞没。只有一张照片上面有那些冲下山坡、朝着他来的那群人;这可以理解,因为一见到他们,他就着急地要回车里去。研究着这张照片,他发觉他们比他认为的要近得多。很明显他们一直在那儿,只隔了很短的距离,而他因为震惊于城市的遭遇,没有注意到他们。如果他们更安静些的话,就可能在他发觉之前扑到他身上,把他压扁。他更仔细地打量照片,发现他们已经够近,一些脸庞都相当清晰了。他猜测着哪张脸才是被照相馆店员认出的那个人的。
他把照片摞齐,重新塞进信封,然后把信封放进他的口袋里。他下了车走到小河边。那条小河,就他所见,不过十英尺左右宽;但在这里,在桥下,它将自己汇聚成一口池塘,岸边已被践踏得光秃,还有几块被钓鱼者坐过的地方。兰德在其中的一块里坐下,打量着池塘。水流冲刷河岸,可能将其下部划出了口子,而栖息在那儿,那条口子里的,则会是那些鱼儿,被如今缺席的钓鱼人所向往的鱼——他们把虫子吊在长杆一端,等它上钩。
这地方被一棵长在桥下岸边的大橡树所遮蔽,凉爽宜人。从某个远方传来了割草机柔和的喀嗒声。水面荡起了涟漪,是鱼儿在吞食浮虫。一个停留的好地方,兰德想。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的地方。他试图让脑子一片空白,将那些记忆和照片赶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假装他毋需思考什么。
但是,他发现,他必须作些思考。不是关于那些照片,而是昨天斯特灵说过的一些话。“我开始想,”他曾说过,“假若一个人走得够远,他是否能把一切都甩到身后?”
一个人该是多么绝望,兰德想,才会被迫提出这样的问题?又或许根本不是绝望——只是焦虑、孤独、疲倦了,看不到尽头。要么是那样,要么就是害怕将来会怎么样。也许,就象知晓了不几年后(不会是很多年后,因为从有人的那张照片里,那个店员认出了一个人),一枚弹头会袭击一个爱荷华小城,将它夷为平地。倒不是它有什么该被轰炸的理由;它既不是洛杉矶、纽约、华盛顿,也不是大港口、运输或通讯中心,它没有大型工业联合体,也不占政府席位。单纯因为而它在那儿,所以被炸了,由於误操作,故障,或者计算失误而被炸。其实这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当它被炸的时候,这个国家或许这个世界可能都已经不在了。几年以后,兰德对自己说,就会发生那种事情。在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之后,世界就会变成那副样子。
就是这类事情让一个人想要逃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忘记它曾经存在过。但说到逃避,他想,这太空泛了,应该找一个起点。你不可能随便找个地方启程,就能逃避开一切。
这是个无稽的念头,被他与斯特灵的谈话所激起的念头;他懒懒地坐在那里,坐在河边;而就因为它带着一丝非凡的吸引力,他在脑海中抓住了它,没有象人们通常对待散漫的念头一样,让其立刻溜掉。他坐在那里,脑中想着它,而另一个念头,另一重时空也溜进来与它做伴;突然间他知道——没有一点疑虑地,实际上也没有经过思考,更不是刻意去寻求答案——他该从哪里起程了。
他绷紧身躯僵硬地坐着,一时被吓到了,感觉像个被自己那下意识的幻想套牢的傻瓜。因为,就常识来说,它只能是幻想。一个挫败者走在无尽的马路上找工作时的苦涩奇想,因照片所示的震惊,以及这口荫蔽的、似乎远离那个坚实世界的池塘所具有的某种奇怪的催眠效应——所有这些集合起来产生了这种幻想。
兰德支起身体站起来,转身朝汽车走去,但就在这时他仍能从脑海中看见这个特殊的起点。那时他还是个男孩——有多大?他回想着,大概九或十岁——他发现了那个小山谷(算不上一个峡谷,但也不完全是山谷),它就在他叔叔的农场下边朝向河流的方向上。以前他从没去过那里以后也没再去过;在他叔叔的农场上,总有太多的杂务,太多的事情要处理,根本没有时间去什么地方。他试图回想他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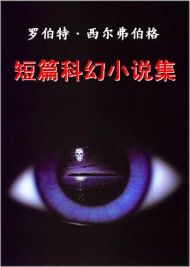

![[罗伯特·希克利_孙维梓] 寻找爱情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