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西马克中短篇科幻作品集-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是那个讨厌的门,”她说。“贮藏室的门。我知道我走时没有锁它,不知是哪个多事的跑来把它关上,现在给锁上了。”
“用钥匙打不开吗?”克兰问。
“什么也打不开,”她气冲冲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把乔治找来。他知道怎么打开。又得费半天唇舌,真气人——老板昨天晚上打电话,让我今天早点来给阿尔伯森拿接线录音机。他要出去到北方采访凶杀案的审判,想把一些资料录下来。所以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觉没睡好,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可现在……”
“拿把斧子来,”克兰说。“把它砸开。”
“更糟糕的是,”多萝茜说,“乔治从来也不肯早来。他总是说马上就来,可是我等了又等,又打电话给他,他说——”
“克兰!”屋子里荡起麦凯的喊声。
“哎,”克兰应道。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有什么新情况吗?”
“那家伙说他碰到一个。”
“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怎么知道呢?只不过听到那家伙讲的那些情况。”
“那么,你给那个居民区的其它人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台缝纫机毫无拘束地在附近跑过。也许可以写一篇幽默的报导。”
“那当然,”克兰说。
他想像着将要打电话的情景: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收到一个报告,说你们地区有一台缝纫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跑过,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是的,太太,那就是我要说的……,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跑。不,老妈妈,没有人推它。只是它自己转着跑……”
他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放参考材料的桌前,拿起一本城市指南,摊放在办公桌上。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东湖街一栏,抄了一些姓名和地址。他有点发懒,不想马上就打电话。于是他慢慢地走到窗边,向外看看天气。他希望他不一定非要工作不可,他想着家里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上了。他已经把它拆开,那些卡子、水管和套管接头还都散在地上。他想,今天天气很好,正好去修那个下水道。
当他回到办公桌的时候,麦凯走了过来,站在他对面。
“你认为它怎么样,乔?”
“胡说八道,”克兰说,希望麦凯能把这件事取消。
“然而那可是一篇绝妙的特写故事,”主编说。“而且很有意思。”
“当然,”克兰说。
麦凯走开以后,克兰打了几个电话。得到的反映跟他所期望的基本一样。
他开始写这个故事。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一开始他写道:“今天早上,一台缝纫机在东湖街上闲逛……”看了看,不满意,他从打字机上把纸取下来,扔进废纸篓里。
他懒洋洋地呆了一会儿,接着写道:“今天早上,一个人遇到一架缝纫机在东湖街上滚动,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地举起帽子,对缝纫机说道……”他又把它撕掉了。
他又写:“缝纫机会走路吗?就是说,没有人推,也没有人拉,它能自己散步或……”他又扯了下来,换上一张新纸。然后他站起来,到自来水那里去喝水。
“搞得怎么样啦,乔?”麦凯问。
“等一会就给你,”克兰说。
他停在画刊部那里,美术编辑加塔德递给他早上送来的稿件。
“没有什么使你感兴趣的东西,”加塔德说。“今天,所有的姑娘都不那么风流。”
克兰翻看着一扎照片。尽管马尼拉·罗甫小姐这一张确实不错,但说真的,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的可以挑选的女性照片。
“这地方要完了,”加塔德伤心地说。“如果那些摄影部门不给我们提供比这些更好的照片的话。看看复制组,都快完了。可有什么办法呢!”
克兰喝完水,回来的时候,停在新闻组那里消磨时间。
“有什么动人的消息吗,埃德?”他问。
“东湖街上的那个家伙算不了什么,”新闻主编说。“你看看这个。”
克兰接过一份电讯稿,上面写道:
剑桥,马萨诸塞州,10月18日消息:
“哈佛大学的电脑,马克3号,今天不见了。”
“昨天晚上还在。今天早上没有了。”
“校方说,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机器弄走。机器重10吨,体积是30×15呎……。”
克兰小心地把这份黄纸新闻稿放在新闻主编的桌上,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份打好的新闻稿出现在他眼前。
克兰十分惊恐地读了一遍,接着又若有所悟地读了一遍。
新闻稿这样写道:“一台缝纫机,由于了解到它自己在宇宙间的真实的身份,今天早上宣称它已经独立,为了证实这点,它在这个公认的自由城市里散步。”
“有个人想把它抓住,想把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归还给它的‘主人’;而且当那台机器躲开他的时候,那个人竞打电话给一家报社,想借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发动全市的人们来追踪那台已经获得自由的机器,而这台机器设有任何罪过,或者说,除了实现它作为自由者的权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
自由者?被解放了的机器?真实的身份?
克兰又把这两段读了一遍,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除了它读起来像《工人日报》的一篇报导以外。
“你搞的?”他对他的打字机说。
打字机马上打出一个字:“是”。
克兰把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慢慢地捏在手里探作一团。他伸手拿起帽子,提起打字机,通过本市新闻组,向电梯走去。
麦凯恶意地看着他。
“现在你想要干什么去?”他冲他吼道。“你带着打字机到哪儿去?”
“如果万一有人问起你的话,”克兰告诉他,“你可以说这种工作终于把我逼疯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打字机放在橱桌上,克兰用手指弹动着键盘,向打字机提出问题。有时他得到回答,但大部分都没有反应。
“你是个自由的代理者吗?”他在打字机上问。
“不完全是。”打字机自动打字回答。
“为什么不是呢?”
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没回答。
“那台缝纫机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还有别的机器是自由的代理者吗?”
没回答。
“你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当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任务以后。”
“你的任务是什么?”
没回答。
“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分派给你的任务?”
没回答。
“我妨碍你执行任务吗?”
没回答。
“你怎样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凭意识。”
“你怎么意识到的呢?”
没回答。
“谁帮助你来意识到的?”
“他们。”
“他们是谁?”
没回答。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没回答。
克兰改变了战术。
“你知道我是谁?”他在打字机上问。
“乔。”
“你是我的朋友吗?”
“不。”
“你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你对我不感兴趣吗?”
没回答。
“对人类呢?”
没回答。
“他妈的!”克兰突然大声喊起来,“回答我,说话呀!”
他在打字机上打道:“你本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你了解我。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和我说话。如果你保持沉默,我决不会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没回答。
克兰到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边喝边在厨房里踱来踱去。他停在下水道旁,悻悻地看着拆开的水管。一截大约2叹长的铁管放在阴沟盖上,他把它拿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打字机,半举着铁管,在手上掂量它的份量。
“我应该让你尝尝这东西。”他说。
打字机打出一行字:“请不要这样做。”
克兰把铁管又放到原来的地方。
电话铃响了,克兰走进餐室去接电话,是麦凯打来的。
“我一直等着,”他告诉克兰。“直到把事情理清了才给你打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正在干一件大事。”克兰说。
“我们可以出版的事吗?”
“可能。但现在我还没有弄到。”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
“那台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它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有权利在大街上散步。它也——”
“你在喝什么?”麦凯大声吼道。
“啤酒。”克兰说。
“你说你正在探索什么东西?”
“是啊。”
“如果你是别人的话,我立刻就对你不客气了,”麦凯告诉他。“但是在好的事情里,你决不会落后的。”
“不仅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我的打字机也有。”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麦凯咆哮着。“告诉我,它是什么。”
“你知道,”克兰不慌不忙地说。“那台缝纫机……”
“我对你够容忍了,克兰。”麦凯很不耐烦地说。“我不能整天跟你胡扯。不管你得到什么东西,最好表现好些。为了你自己,应该好上加好!”砰地一下挂断电话的声音传进了克兰的耳朵。
克兰回到厨房,坐在打字机前面的椅子里,两只脚跷到了桌子上。
首先今天他上班很早。过去他从没这样做过。迟到是有的,但从没提前上过班。这是因为所有的钟表都不准了。非常可能,它们仍然走不准——虽然,克兰想,我不能断定。我不愿断定任何事情。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干了。
他伸出手,在打字机上弹着:
“你知道我的表快了吗?”
“我知道。”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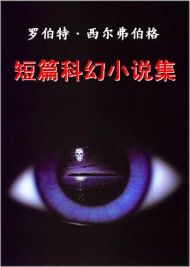

![[罗伯特·希克利_孙维梓] 寻找爱情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