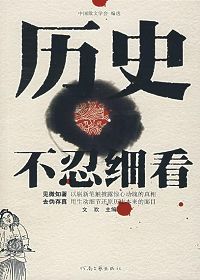�ƴ���ʷ�о�--��ɦͷ�ж�ƪ��-��1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ˡ�������ǿ��ɢȥ�ľ��䲢û�����������뵱Ȼ����������ȴת������ççɽ�֡����ֳ�����DZ�����������������ֵ�ͷ��Ѫ�����������������Ϥ�������ġ���͢����Ϊ�����ṩ������������ԡ������dz�͢��Ȼ�Ķ����棬Ҳ����Ȼ�IJ��䡣
����ר��IJþ�����������ʮ��ƻ�û�б��ó��ĺ�˷���䱾������һ�롢��һ�������ҲͶ����Ũ�ص���Ӱ�����DZ����Ӿ���Ϊ����֮��������֮����������ȴ��֪����ʱ���ó������˾��䵽�Լ�ͷ�ϡ�ϰ����һ��һǹ��ȡ��ʳ������������������˺�Ȼ�����Լ��Գ�͢�ij�����˳û�л����κκô���������������Ƶ���ǰ;δ���ľ��ء����Dz����������궯�ˡ�����ʵ�ʵ�������Ϊ����ǰ�������ź�˷���˵ľ��˾��Ѿ���������Զ�͵��ӳ�͢�ˡ��������������˳�ͷ��β�İܱʡ�
������˷����ͬ�ڵ۹������ݿ�֮������������������ͳ����Ƕ��̶Ⱥܵͣ����������۴Ӿ��û�����Ȩ���ṹ�������Ļ���̬�Ͽ����ࡢ�ԡ�κ���Ѿ������ˡ�������Ҫ����ģ������ǽ��Լ���Ȩ��֮�����������˷������һԪ���۹���ȫ���ؽ���ǰ��ֻ�����Ǻ��ߵ�������衣Ԫ��������ս�����������裬�����ѵĺ����������ڿɻ�û�����ü����֡���嶵ij�͢�϶�����Ϊ���Dz���������ɨβ������������������ڽ������������һϵ�д������������һ������˲��������һ������
����������һ�η���ּ�⣺��κ���ڶ������ʹ�γɵ½ڶ�ʹ���ɵ½ڶ�ʹ����Ԫ����ɽڶ�ʹ����ɽڶ�ʹ����������ڶ�ʹ�������ڶ�ʹ�����κ���ڶ�ʹ����������Ķ����ﲼ���κ����ڶ�ʹ��һ������˴��ģ�ص��������Ա����Ҫ˵���ƣ�����ʢ��Ҳ�����й���������֤����ֱ����ʱ�������ڵ۹����������������м����Ȩ��������ָ��ܱ����۲��۵�ִ�С��Ȼ��Ԫ�����˵Ľ������������Ҳ��Ϊ���жϽڶ�ʹ������ط��������е���ϵ������Ԫ�����˵ļȵóɹ�����ϧ���ǣ�������ԸΥ�س��˶���Щ�ɹ��������ġ��ͳ�������һ����һ��ӱ����Ͻ��ܺõľٴ��ھ������ʱȴ��������
����ּ��һ�£�����Ὣ����Ԫ���������跴���������Ϊ�ɵ½ڶ�ʹ����������ʡ�����������������ǶԵģ���Ԫ�ͳ��������һֱ�dz�͢����ʵ�Ľ������������쵼κ���������˺�˷����Ϊ��Ԯ���Կ���͢�ľ��档�����¬���ͳɵ���˳�����Ī��ѹ�����������Ч�����ظı��������ںӱ���ս�Ա�������������Э����͢�ַ��ɵµ�������ս�У������Ҳ�����˽����˲����Թ����Ԫ��ʮһ���Ϲ�֮�ۣ��ɵ¾��ж�ǧ�������������²�Զ�����ǵ�Ȼ���Ȼ�ڻ�����͢ȴ������ʵ�����������ɵ¡�
�����ҵ�Ŀ�ⳤ�õ�ͣ������ʷ����һ�С��ƺ�������������ˣ�˭�����Բ��������������һ�С���ôҲ�벻���ף�Ϊʲô�̶�һ����ʷ�������֮��Ĵ�������ûͷû�ԣ�û��ͷ��������һ�֡�������ˡ���ãȻ��ãȻҲ����Ȼ�����⣬��������֮����߷����¡��������Dz�����˵�����Ƕ����߷����²�����̸���䡣
����������Ǵ���������ε����������ɵµġ��������εģ�������ǧ��κ���������ױ�����������Ϊ�����Լ��������������ˡ�����ǧ��פ�����ݣ���Ȼ���ܵõ�κ���Ĺ������ɳɵ���û�����ǵı��ơ����Ǹ���û��ָ��������Щ��Ϊ�Ͻ�Ӭͷ���ò��ɿ����Ĺ��š��������ɴނ���Ȼ�ܾ�Ϊ���Ե�κ�����������������������������Ȼ����ɵ£�������ȻӦ��������ͳ˧��������ĵ����ƺ���С�����������ȥ������κ����ɵ�˵����Ķ���ԹԹȴ����˴���غ����ˡ�������ͬ����һ�����ނ������һ��������ԭ���Ͻ�û�д���ȴ����ʵ��ȥ��Զ�������������ֱ��Ĵ���ʵ���Ǵ��г��쳯���ε�����������
��������������ʵ����ķ����£������������ˡ�����վ�ڹ³���Ŀ����ǧ�ױ�����Զȥ���������Ŷ���һ����Ȼ�糱������ǵص�ӿ��������ûŮǽ����û��ܦ����û���ݰٳ���¥��������û�����Լ���
�������ã����������������ͬʱ���ѵģ�����Ļ�š������������ˡ�
����Ҳ��������У���������������������ȼ���ҹ̸ʱ���龰����������Ϧ�������������Щ�̻壬������������ѹ���������һ��������¡��������ձ�û��û�εij�͢�����������ƻ��ij����м䣬��Ϊ�����ҳ϶��е������ô�������ţ������֮�����Ƴ�������߽��������ص�Ӱ�졣������Ժ���ʲô����Ľڶ�ʹ������Ч�ҳ�͢�������Ǻ�˷���������ط��������ĵ�ʼ����һ�������ڲ��ϵ��������ǡ��������������ǰ�İ�����һ������˳����ֵ��˵��������������������ģ�����Ҳ����������ʮ�������Ʈҡ�ij�͢��һ��Ͷ������Ŀ���ʱ��������Į�ر�����ȥ��
����ɱ�����������������ͥ�գ�һ��ϲ���������ȡ��İ���˼�ֻ����ˡ���ǿ�ȼ���¹���Ω��������⡣���߳�ŭ�ij�͢��Ȼ�ܾ��������漴��κ�����ả�����塢�Ӷ�������ȸ�·�����ּ��������ɵ¼��ᡣ�����ܲ�������б�ֱ�������������һ��ֵ�û���������ʽ�ս��ˡ�
����ʱ�����ս�����Ҫ����������ġ�ѳ���ߵ�һ���������Ǹ�������ʱ��ϢϢ��أ��������Dz�δ��Ϊ��ʱ�������ϵ�û���ɥʧִ�ţ���Ϊִ���������츳��Ʒ�ʡ���ֻ���������˲��ܡ��Ż�ѳ���ڼ�����ȥ��ʱ����
������˵�����ﲼ��������Ķ��ӡ�����ج�ĺ���Dzɢ��������ӡ��輿ӥȮ��Dzɢ������������־��ѳ����ĵ�һ�������Ȼ�ط�κ�����ﲼ���ͱ�����ӡ����ʹ��е�ʱ��˵��
��������ӡ�
�������������ü����ǿ������ߵ�������
�����ﲼ��ȥʱ��ľ���ʹ���ǿ������Ǹ����������û�������Ϻ�˷�������Ժ�ʱ�ֵ��Ͼ����������������ڡ�л�ڽ���������ܹ����ӡ�ɽ��������Ϥ�����桱�����ʵ���ﲼҲ�����������·ǰ��Ԥ�ϵ�����ˡ����ǣ�����ֻ�������ǵı�������ʾ����һ����ʵ���۹�����һ����霳�ӹ�ij�͢�쵼�ţ������͢����ȱ������ȵ������ǻۡ���ˣ���ʱ�ֵĶ�Ϥֻ��ʹ���Ǹ��ӵ����κΣ��������κ�����¶���������еı�׳����������ǵ�ѡ��
�����ﲼ���Ɐ׳�����飬٢�������κ�ݽ����ˡ�
������ʷ���ʱ���������ʱ��˳��һ·��ս�����������㿴����һ�����ֵ�ʱ������Ļ��Ȼ����������������ˮ��������ϣ�����һ���ž�Υ�˵���ף����ǵ�������������ǵ��������ʺ�ֱˬ����¶Զ���������ֵ����أ�����������ô�㷺�����й��������������������������߽���ĸ����·����ڶ�����ʯ���Ƶ������������������еı�������κ���ķ��ˡ��ϳ�������ͱ����Ĵֱɣ�Ҳ����ʢ�Ʊ��滯�İ��D������Ȼ�����ڱ������������˺���֪��ʶ������������ڵ�����һϢ�����ơ����ǣ��㷢�֣���δ���鵽�ĸо��ֱ����ĵ��ﹴ�����������ǡ����굽ij����֮�����ϵ��龳��Ҳ����ͻ�������Ļ�����Ǿ�����ʷ�ĸо���ǰ�������ĸо���
������Ӧ�ý��ﲼ����Ѳ�������䡢����ʵ��Ϊһ�࣬����ͬ������ͥ�����ھ��ص�ţԪ���������ǻ������ż���������������ϣ�����ԥ�á����;��𡪡�Ҳ������ν�����Կ�������ʿ�����ǵ������ִ�ţ����Ƴ��Ժ����س��˴�˵����ž��е����ʣ���ʵ������Ҳ�Ѿ���ϡ���ˣ������Ǻ�ϡ����һ��㣬Ҳ��ע��Ҫ��һ��һ������ġ�һ�����Զ��յ������ǣ��������ﲼ��Ȼ���ѵ�ͬʱ���ź뾸֮�����Ĺ�����θ��ױ������������ݣ��Լ������ڳ������ӱ���Ӧ���ĵ����������ϸ���Ҳ�����������Ĺ�ʿ�ˡ�
�������ǣ���ʹ�Ǵ���Ա��ⷽ����Ѫ�����ŵ�����Ҳ�ݲ��������ˡ�κ����¬�����ɵ±���������λһ��ġ����ǹ�ͬ������һ�������˵���ᡣ��¬���ͳɵ�������Һ�κ����Ȼҡ�������ˡ�κ�����Ƕ���ʮ��ģ�����ֻ������άϵ�������ݿ���ͳ�Ρ�����һ������������ء��챦�����ȷ��ٵľ����ܻ���Ҳ������֮�൱���ѡ���Եİ���ʹ��ʿ���뷪Զ����̬��ɺ�������Ϊʲô�������ʱ�ųƺ���ǿ����κ��ʼ��ֻ��ʱ���е�һö��Ҫ���ӣ���û������ϵ��������Ӷ���ɳ����������Ϊ������Ϊ���ҵĴ���֡��ξ������ҳ�ǰ�е��ﲼ�����Ų��鲻Ը��κ���ڷ�ѩ�п�ʼ�˸���֮�ۡ���Ҳ��֪�����ܼ�Ԧ��֧�����Ѿ���ҡ�ľ��Ӷ�á�
������һ�궬��ķ��ѩ��Ⱥ��ӣ�������צ������ӱ�һ������Ĵ�ƽԭ����������˸�ź�������ݷ���˺ҧ���ﲼ��Ӫ�ݡ�κ�˵������������ޱȵ��Ǻ�����ѹ���ˡ���͢�������캮�ض�����������������ؽӶ������ߴٳ�ս�������߽����ﲼ��£���ĵ�Ŭ��������κ���ر�ǿ�ҵĶ����������ﲼ�ټ������һ�λ��顣��ʱ���������²��ᳬ����ǧ�ˡ����Ľ���Ҳ���ܾ���ս��
�������ӵ�����Զ�ˡ���Ӱ������ﲼһ�Բ��������봱���ʹ��Ļ��ʣ����湩���Ÿ�����λ�������Լ��Ĵ�������������ģ����ڳ���ǰ�����Ѿ����뵽�������ˣ�ֻ��û�뵽��������ô�졣�����ﲼ������ԡ�����Ȼ���ڻ�ƵĹ�����д�����ű������Dz����ǿ���͢�������ƣ����볯͢��Ҫ�ٽ��ҳ�����������ա�ţԪ��Ҳ�����ں�˷�����ƻ����Ѿ��м��ˣ����ﲼ�Լ���Ҳû�д������������
�����������Եķ��

![[����]����ʷ����](http://www.xibiju.com/cover/5/539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