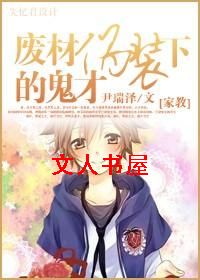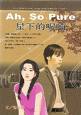������ʷ�µ�����֮��-��2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ϸ������������־���м�����ѧ�����塱�ıʷ�����������־���塷С˵�ִ��С��߷�ʵ�£��������¡��ġ�ʷ����ɫ�ʡ����⣬��Щ��ʷʵ���ڡ�����־���в�û���ᵽ��������֮��ע��д���ġ���������������־���塷��30��д��������Ԭ�ܵ�ıʿ����Ԭ�ܲ��������Ľ��飬������Ԭ����ı�����ܣ�����ס�ܲ��ɳ��������ݵ���ʹ�Ժ���ȻͶ����Ӫ����������̽���ʲܲ����ݻ��ܼ�ֶ�ã���Ի������֧һ�ꡣ����ЦԻ������δ�ء�����Ի�����а�������������������������Ի������Զ����������ʵ�ߣ�������ʵ��֧���¶�������ЦԻ�������˽����ϵ¼��ۣ����ȻҲ��������ЦԻ�������š�������թ�����츽������Ի��������ֹ�д���֮������������Ի���������ң����Ѿ��ӣ����ȻԻ��������֪֮����397������Ű���ܲٴ�����ʹ����˵���������Ǿ����˲ܲ��ڳ����������Ԭ���ڹٶɵ���ʷ���¡���������ĶԻ����̻�������������Dzܲ��ʻ���Ը����������ڽ����˳��ٵġ�����־���ﲢû�м��ش��£��������γ�������֮��ע�£���������Ⱦ��������Ŀ������������Ի�������������г�ӭ֮������ЦԻ����������Զ������Զ���䣧�������¼��ӣ���������ν��Ի����Ԭ�Ͼ�ʢ�����Դ�֮�����м�����������Ի�����п�֧һ�ꡣ����Ի�������ǣ�����֮����Ի������֧���ꡣ����Ի�������²�����Ԭ��а������֮��ʵҲ����Ի��������Ϸ֮������ʵ��һ�£�Ϊ֮�κΣ�����Ի�������¾����أ�����Ԯ�������Ѿ�����Σ��֮��Ҳ����Ԭ�������������ڹ��С��ڳ����;����ϱ����������Ϯ֮�����������������ۣ��������գ�Ԭ����Ҳ����398��Ȼ������С˵�еĴ˴���д������������ע�Ļ���������Щ�����ļӹ�������ע��д���������Ѿ��롰���塱�ıʷ����졣���磬�ܲٴ��Ԭ���Ժܲ������ѵ�����ԭ������Ա��Ԭ�ܵġ���֮ͨ�顱��������־����ֻ�����š����������У������¼��������飬�Է�֮����399����������������С˵�У�����ϸ��չ������ɡ�����Ի��������һ����������ն�ɱ֮������Ի��������֮ǿ��������Ա��������˺�������������֮���������ʡ���һ�仰���Գ��ܲٵ��ؽ�����ı��
��������������������ʷ����С˵����������һ����������۵����ʸ���ˮ�棺��һ�����ʣ��������ڡ�ʷ�顱�С���ȥ����������֮��ע����ӡ��������ʷ�������Ƿ�ʷʵ���ڶ������ʣ��˴�����ע����ʷ����С˵��������������������ʣ�����עд����ʷ���ʷ������е�С˵��д�к��죿���ĸ����ʣ���Ȼʷ��д��������ˣ��Ƿ�С˵�ʷ�дʷ��Ϊ��ȡ����Ϊ������ƪС˵���������塷�Ķ���Զ�ȿ�ʷ�顶����־���Ķ��߶�öࡣ
������С˵�ֱϾ�������ʷ��������ʷ��ʵ�������������ɣ���������һ�����Ե��͵�ì�ܡ����������˵����һ����ʷС˵��������ʷ����ʷѧ���������ʶ����һ�㡣��Ҳ��ϲ��һ����ʷС˵������ij�̶ֳ���ȴ�ر�������Ϊ�����ڹ��������ʷѧ�����о����¼������������ԭ����ʷС˵����Ϊһ��������ʤ������Ϊһ����ʷѧ�ҡ������������˵����ʷѧ�Ҳ���һ�������ҡ���������һ��С˵�һ�ʫ�ˡ���400�ԡ��������塷С˵����������Ϊ�����ڡ�����־���С��ԶȻ���������Ϊ���ˣ�Ω����ղ�������401�����ɣ��������б��£�Ϊ����ѭ�����������������ɣ�ֻ������ʷ����ʵ�����������ԩ����������խ������������Ҫ�Ը��ص㡣�ɼ���������һ���ϣ������dz��ٵĵ��ˣ�������ʷ����褴�������;������ʹ���ԩ���ƺ������ң���������ƽ����ѩ֮�ա��������ʷʵ��С˵����ʷ������ò������褣����������С˵�е�����������Ҫ����ۿۡ���Ϊ�������������塷�Ķ��ߣ�������˵��Щ����ΪϷ��С����������Ӱ���Ϸ���ǣ�����û���˻�������Ǹ�Ϸ���Եر��������������褣�������ʷ����ʵ�������褡��������������ӣ��ڡ��������塷�ﻹ�кܶࡣ��ʷ����ѧҲ����Т����ȫ������Ҫ��һ�㵱Ȼ�ǣ�������־���ǽ�����д�ģ�������־��������ѧ�ʷ����ص������쳣�ĶԻ������ɾ��п���ʷ�����������ʣ�ͬʱ����������������롰����ʷ�������ʮ�������ġ�����С˵���������塷����ߡ�������ܡ���������ʷ̬�ȣ���������Ϊ���ؾ��������������������д�������Ѳܲٿ̻��ɼ�թ�ޱȵĹŽ�����е�һ���ˣ������д�ɼ��Ͷ��ܵ�С������
�������ǻ��ڴˣ���������ʱ��ʼ���Ű���ʲ���صĶ���Ԥ�ԣ�����ѧ����ʷѧ����ȫ�µĽ�Ͻ���Ϊ�¸����ͣ�ָ21���͡���������������ľ��б�־������¼������ֽ�Ͻ���Ϊ��ѧ֪ʶ��һ����ʽ����Ŀ�IJ����ڶԹ�ȥ�ĸ��������ר���о��������ڶԶ��߽��������ۺϡ�������������֮����ʷѧ�ҵ���������Ϊһ����ѧ��ʵ������ʷ��ʶ��Ϊ�������������˼����һ����ʽ�������������γ���������ý�Ϊ��ʷѧ������ȣ������ʷѧ������ʱ���Ի�ʱ������Ը��Dz�Ը�⣬������ֻ���Dz����Լ��о��ɹ�������Ҳ���뿼�Dz�����һ�ɹ�����ʽ�������ǵ��о��߸е��б�Ҫ����߷����������ȥֱ�ӽ���ʱ���������ָ���ʱ����402����Ϊ��������ʷѧ������֮һ��³��ѷ������ָ������ʹ��ʷѧ��ֻ�Ǿ�����ʷ������������ȷ�пɿ����¼�����ô�������������ͻ�ȱ���������á��������ŵ���ڣ�����Ͳ��ܱ��һ�������Ĺ��¡�����ͬʱ������ǿ����ʷѧ�ҵ���ҵ������ѧ��������ͬ�������õ��ǿ�ѧ����������������ѧ����������������ְ������Ӧ�������о���ȥ�����¼��ļ��ɣ������ɹ���ʹ����ȫ���˽��ȥ����403��������ֿ�ѧ������������ѧ�����������ַ������ܹ�̽������ġ�
����������ʷ��������ʷ��3��
������ʷ����ѧ�ڶ��Թ�ϵ����Ȼ������ʷ����ѧ��Ҳ������˼��Ĺ�ϵ���ڿ�����¿��������е�һ�Թ�ϵ����ʷ��������ʷ����Ϊ������˼��֮�⣬�κ����ﶼ����������ʷ��������������ĸ��鶼�Ǻʹ�����������֮�е�������������ľ�����ϵ��һ��ģ�����Ϊһ����ѧ��ʽ�Ĵ��ǣ�������������鲢���ܹ�Ӧ���������ʵ���ʳ�����Ⲣ������ʷ�����У����ռ�����ʵ���������Ļ��ڻ���¼���������ֱ�Ӿ��鼰��о�����ĺ����ļ�¼��Ҳ������ʷ��������õľ���ʫ�裬������ľ���һ��ͻ���������������壻������Զ����������ʷ����404�ڿ���������ʲô����ʷ�أ�����ʷ��֪ʶ�ǹ��������ڹ�ȥ������ʲô�µ�֪ʶ��ͬʱ��Ҳ������������£���ȥ�������Ծͻ������֮�С���405��������֮���ǣ���ʷ��˼�������������֮��Ҫ����ʷд��˼��ʷ�������塣��˼��ʷ������ȫ��ͬ����ʷ����Ҳ����Ϊһ���ܰ���������������ѧ�Ƶ�˼����ӻ⡣
�������ԣ�˵���ң�����������˵�øɴ����䣺����һ�仰����ʷ��Ŀ���ڽ���ȥ������ʵ������������¼�ֵ���Թ��ִ��˻֮�ʼ�����406��Ȼ������ʵ��ʷ�Ҷ��ڹ�ȥ����ʵ��ʮ֮�˾�Ӧȡ���ɵ�̬�ȡ���407��Ϊ�����������⣬����ȥ���������¾���֤����ʹ�������ŵ��£����Ǹ���֤�����ŵľ�����ʵ�ԡ���������Ȼ�Ǵ���ġ�������������ȥ�������������£���Ȼ��������ijЩ�����֤�������������ŵ��¡�����ͬ���������ڴ����ռ�����֤�ݳ���������и�ɻ������۵Ĵ���ʹ�������κ�ʱ������������Ϊ�г�ֵ�֤����ʹ�������ŵĶ�������ʹ������Զ���ܽ�ʾ��������ͬ���������ŵĶ���֮��IJ�������Ȼ��ˡ�����ӵ�е�֤�ݲ����ܱ�֤����ӵ�������������������������ĵ�·Ҫͨ��֤�ݡ���408�¹�����˼��Һն���ָ������������ΰ����ʷ�¼��У����Ƿ���������һ���������ɣ�����ǣ���������������ϣ�����ʲô�ط�������ʲô���飬���ǻ��ڸõط��Ļ�������Ҫ�����ڸ�ʱ����������ԭ�����������Ļ������Ը�409�������Դ��������Ļ�����������Ƿ����ڡ��ĸ�еġ�����֮������������ˡ�������������������֮�����������о����ĸʱ���õط��Ļ�������Ҫ��������ʱ����������ԭ������������������������Ը����Ե���Ϊ��Ҫ����Ȼ��ͬʱ�����о����ᵱʱ�ġ�������������Ҫ����������������ԭ�͡��Ը��ڸ��˵������ʷ�ϵ��±������ͬ�������ձ�ġ����ڵĶ������±����ϵֻ��һ������ʹ������ʷ�������ڡ���ȥ�������ڡ����ڡ�����410����ʵ�Ѿ�������ʷ�ǵ���ʷ����ζ��
����Ȼ�����á�����֮�����Ŀ�����ʷ��˵��Ҫ̽������ȥ���ġ���ʷ�±䡱�������ģ��Լ������ڡ�����ʷ�������������ģ������ܿ���ͳ�ġ�����ʷ��������š���Ϊ���������������ںܴ�̶��ϣ��ȸı��ˡ���ȥ����ҲӰ���ˡ����ڡ�����������Ӱ�쵽δ���������Ǿ�������˿������Ϊ������ֻ�����Ŀ���࣬���ޡ�Ī���������ң�������������ʷ��ʱ���ܲ�������ְ��������ˡ�����ʷ�������ʷ���������ֽ���ʷ�������˵��
������������Ҿ���ǿ�ҵ���ʷ��ʶ���������ѧ����γ��и�����ʷ����Ҫ��λ�Ͳ���Ϊ�档���ӱ��˾��������ij�������ߣ��������ӵ�˵�������������������ֻ���������ġ���������ࡣ�������һ���Լ������³����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