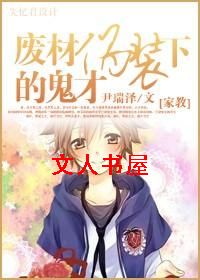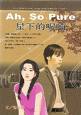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他就比较容易解释了。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档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他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了历史记忆。”386我当然明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指出的:“每个人目前的立场都会决定他对过去一切事件的信念。”387他对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是“批判”,他说:“假如每一种记载都是可靠的和信得过的,假如在人类进步的发展中,一系列分散着的见证人的判断都是确实无误的,而且不加修改就可以构成为一个和谐连贯的整体;那倒会确实是奇怪了。”388但无论如何,我采访“老舍之死”搜集来的这些第一手的“口头证据”,理应为未来最挑剔的史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者所共享。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1)
历史与诗到目前为止,“老舍之死”的历史几乎都是由与“八·二三事件”相关的人们的“记忆”构成的,这倒极其符合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从这三种源泉——记忆、想象、理性——产生了三个产品:历史、诗和哲学,别无其他。”389在这三者关系中,第一对关系是历史与诗,也即是文学的关系。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专门谈到文学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他说:“什么是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390像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部分只占50%,另外50%是他自己找材料印证补充。而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李宗仁的口述部分只有15%的篇幅,其余85%都是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他认为,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到60%左右;非学术人的口述史料只有15%到20%左右。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在于: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漫漫谈,漫漫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391但我想以“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来说明,死无对证自不必说,因为谁也没本事让死人还阳作证,但活人活口并不见得就能够对证。像我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的时候,很多人叙述起来,都十分愿意把自己的“记忆”描绘成根本无从考证的“孤证”。换言之,在某一点细节上,他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也许当时情形真的是如此,但仔细一想,以“八·二三事件”的性质,“唯一”的几率不一定高。这当然纯属我“小人心”的忖度。我还是想举那个最极端的例子,即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那三位打捞者,这三个“唯一”哪个才是真的唯一呢?或都不是?不是活无对证吗?不过,“唯一”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否定了对方,同时可能也已经否定了自己。
论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六经皆史”是清代章学诚说的,认为不只六经,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刚更有发展,他认为不光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史皆文”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散文。难怪鲁迅称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说:“每一次,当历史学家不仅要弄清历史事实,还要对过去的事件做出鲜明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时,他的著作就会变为历史散文。在许多世纪里历史散文与文艺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把历史作品与文艺作品两者分割开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起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最终完成,而在整个20世纪里,历史科学与小说才各自以独立的形态存在。”392如果历史不带任何文学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叙述,势必变得干瘪、苍白,死气沉沉,也会随之失去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唐德刚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回忆录》举例说,在西方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他与希特勒相约见面,但由于他失言批评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气之下取消了约会。两人始终未能谋面。这件事如果由史官记载,或许是直白的日志式的一句事实:“丘吉尔本应在某年某月某日与希特勒在某处会面,后因希特勒取消约会,两人始终未曾得见。”这当然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可《丘吉尔回忆录》却以文学的妙笔这样写到:“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losthischancetoseeme!)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气,活了起来。读者也会因此而喜欢读历史。
至于“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外的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现代人写史,似乎已不太讲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刚以英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为例说明,美国人写史大都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而英国人写史就格外注重文学修养。英国人写史一定是英文写得漂亮,美国人只看重正确与否。他认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由于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味,在研究中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当资料看可以,但让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把它们当文学看就缺乏可读性了。似乎“历史学家极少关心自己著作的文学形式问题,完全不考虑在此期间成为私生活叙事文学的小说本身及其文学形式的变化。而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在写作时违背历史事实,认为杜撰是自己的权利。然而正是他们把有关过去的观念灌输给非专业读者。他们不仅美化了过去,而且复活了过去,使读者把过去的东西延续到今天之中。请您自己来判断事情是否是这样: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的,而很少来自专家撰写的纯学术著作。”393史学家汪荣祖也指出:“近人写历史文章,多主平铺直叙,以求客观公正;尤其是所谓‘科学派史家’常将文章写得像数字一样呆板,像表格一样整齐,以为如此才‘正经’、才‘正统’。在此种风气之下,文采便难被史家所取,好像一讲究文采,就联想到主观渲染,渲染当然就不客观、不科学了。其实,文采非即渲染,真正的史学佳构仍然需要文采,……史家之文采即取决于:如何以适量的文辞,完成著述之目的;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说清楚来龙去脉,以及议论的重点。……孔夫子早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很可作为史家的座右铭。”394唐德刚显然对此深有同感,他不满于这种美国式的现代史学趋势。在美国,历史现在叫做Socialscience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被“科学所污染”,变成干燥无味的东西了。更有甚者,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外,最糟的是电脑普遍应用之后,历史已被电脑征服了百分之七八十。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以前学者皓首穷经一辈子搜集的资料,用电脑几十秒钟就可检索出来。他认为,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无异于历史的自杀。学历史的人,人生也再无意义可言。而现阶段历史中很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口述历史,这可以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会有很高的可读性。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2)
因而,唐德刚特别强调,做口述历史的人,一定要有文学素养。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395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格外强调“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历史著作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感兴趣。”另外,历史学家不必担心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描述的人物有褒贬,因为如果要让读者感兴趣,必须得在戏剧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396史亦小说由唐德刚所说刘、关、张三兄弟,我忽然想到作为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事,三分虚事”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