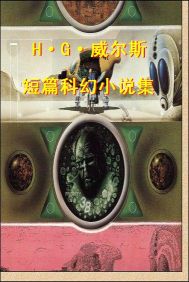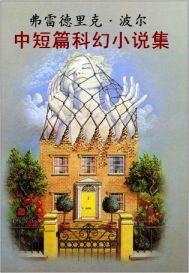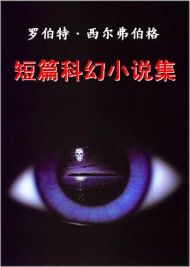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十一辑)-第2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个女人!”
男男女女的形状走进夜色中环绕在她身旁……
她回到她的房间,月光照进来,照亮了她的身体。她呻吟着猛烈地拥抱卫门。
“先生,你要杀死我了!”
一听到卫门的声音,吉村小姐立刻恢复了常态——领悟到她又进入她的幻想了。
(卫门,卫门,为什么你不长大?)
日子过去的时候,矛盾在卫门的头脑里形成了:在每个人的心里,包括他亲爱的先生的心里,都隐藏着那个丑陋的东西,一种想拥有别人身体的不同寻常的欲望。为什么?卫门并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仅仅是他希望看到的东西。
每个人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孩子们出生了,我早知道那个了。但谁是我的父亲?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一直坚持搜索村里人的思想,而且当他继续收集了和他母亲有关的其余点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事情的真相似乎是这样的:她逃入她的疯狂世界是为了逃脱某种可怕得无法言述的东西。
在大仓库的管理员那儿他找到的是:(阿千的宅子……人们说它以前是一栋鬼屋,后来阿千总是在叫唤。不,想想这件事,它不是她母亲吗?她的祖父被杀了或过世了。那就是她发疯的原因……)
竹夫人的思想一度悄悄说:
(我死去的祖母曾说过,他们在那里藏了一个发疯的外国男人,他奸污了阿千,所以他们杀了他,或者是类似的事……)
伐木人德抱怨的想法描绘了一个更惊人的情景:
(外祖父看到过那景象。阿千的宅子全是血,每个人都死了,被谋杀的。无论如何那个家族代代有疯病。阿千的父亲——或者是她的兄弟?病得非常厉害。在所有被砍得乱七八糟的尸体中间,阿千正在玩球。)
年纪一大把的源氏也知道故事的一部分:
(听人说很久以前,小山上现在宅子所在的地方,着火的柱子从天而降。自那以后,所有美丽的姑娘都出自那一家,一代又一代。而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话,那是传说。)
很久以前,忘掉是什么日子了,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千是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且疯了,成了村里的公娼。这是卫门能够了解到的全部事实了。
六
人们说时间冲刷记忆:事实是,记忆负载着岁月的重负,被压成了坚硬的、钻石般明晰的东西。那个村庄沉睡着一个秘密,而且它还在那里静静地安眠。多年来我的思绪围绕着这些令人迷惑的事件逐渐冷却,但秘密将永远无法揭开——除非我去那儿认真地调查。
我多次尝试要回去。一年前我到了离村子不到50公里的地方,之后,因为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我转了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有更好的理由去那里。在开始这些旅程之前,我总是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厌恶感所征服,就像是有一种催眠术似的强烈冲动迫使我不再接触那个地方。
另一个奇特的事实:
在我驻扎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里,我回忆不出曾有任何从“外面”来的人在村里停留的时间超过几个小时。村里人认为我是第一个整整在村里待了十年的外来人。村里人中唯一曾在这个孤立的范围以外居住过的是竹夫人和吉村小姐,她们曾经离开这里去上师范学校。
如果去那儿,我确实计划完全进入那个村子。我感觉当地人肯定会阻挡我回去,除非我有军队的命令。
那儿有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支配着这些事件呢?
这样一种力量会有长远强烈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个不到两百人的村子能够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理之外生存。我这么说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这村子里没有一个男人应征入伍。
而谁可能是这种力量的控制者?谁用法术控制了大家?竹夫人,或者老师?如果这两个人都曾在别人的指引下离开过村子,那谁又是这个秘密最核心的人物呢?
那个疯女人,阿千?
当夏天傍晚来临的时候,我的记忆里浮现出无数村里孩子唱的歌。很奇怪的是,那些歌提到的每件事都与村里人声称拥有的历史完全不同:他们说村庄是几个世纪以前、在平安时代平家与源氏的决战中,遗弃了平家而出逃的家臣建立的。从那时起,没有人再离开过这个村庄。但是没有一个在这里流传的故事和平家的传说有关。这个村庄就像是独自沉睡在这片梯田里,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它像历史河流中的小岛,和世界分离。
有什么依然藏在通向阿千宅子的石梯下面吗?“未知的卫门”在绝望中放弃了、而且遗留了一些东西在那儿。一个把水抽上罪人之孔的水泵、或者孩子们玩手球游戏时唱的歌里暗示的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会登上
那些野草青青的台阶——
一——天空中的一道石梯
二——如果它不能飞起来
如果它永远不能飞起来,打开……
当飞行之日到来时,石阶会打开吧?或者你必须打开它们才能飞翔?——问题啊,问题:也许“未知的卫门”的秘密将永远在那个地方沉睡。
还有阿千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一段时间以后,卫门又一次开始他很久以前放弃的尝试——搜寻他母亲的思想。覆盖着阿千思想的奇怪的白雾和以前一样浓重。
(散开吧!)
卫门的思想以一种精神感应的力量猛然震荡开来。
发出一个传心术的指令、把它的意义送接受者的头脑,这种手段可以用物理术语来解释——力量的矢量;然后,又一次,也许只是因为卫门的精神控制力加强了,而且他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意义的本领更加纯熟了。无论是什么缘故,他的命令一发出,在阿千脑海中的浓雾就像被一阵风吹散那样散开两边,卫门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浓雾后面的景象。
她的思想就像无垠的蓝天。卫门飞快地进入、退出了好几次,攫取他母亲的过去遗留下的记忆碎片。它们数量很少,而且缺少一条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每一个场景都像一块破碎的马赛克。
在所有的碎片中只有一个景象是连贯的:一部巨大的机器——或者是大厦——在她身边崩溃,以及当她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的时候爆发出的那种感情,混合着可怕的痛苦和欢乐的感情。
而那是很奇特的:在她与村里男人所有的际遇中,只有这一次经历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永久地在她的记忆中燃烧。
这个男人的面孔和年纪都不明了。他的形象如同海草在海底的洋流中波动。事情发生的晚上,有月光朗照或者有别的什么物体在发光,因为他的身体沐浴在灿烂的蓝光中。阿千知道的所有别的男人,在剥夺她意志、充满她头脑的白雾中永远消失了,只有这个卫门从未见过的男人以一种意愿和热情的力量存在着。那份记忆涌着欢乐的洪水,同时带着巨大的哀伤。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是卫门能明白的了。
一种模糊的想法被搅了起来:这个阿千记得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
正当卫门不知疲倦地搜索着他母亲和村里人头脑中的记忆残片时,吉村小姐在一个幻想世界中玩耍,在那个世界里她兴趣的中心总是阿千。现在晚上睡下的时候她已经习惯抱着卫门,有一个晚上,她的心被成为阿千的渴望吞噬了,想和任何一个男人睡觉,几乎要爆炸了。
她怎么会知道卫门明白她的一切想法呢?
无论谁也没有想到,卫门从他们隐秘掩藏的生活中搜寻到大量多得可怕的纯粹的事实。然而,在这场追求性快感的精神风暴中,他为持之以恒的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卫门认为,除了最小的孩子,村里人个个诲淫诲盗,猥琐不堪,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特别是阿千和他自己——他们是最大的罪人。在那些男人的头脑中,他是阿千时不时的放纵发情的固定产物,生为阿千的孩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深刻的痛苦。她总是把身体暴露给那些男人,然后……
卫门憎恨她。他恨到她那儿去的男人们。在他对于九岁孩子来说是过于聪明的头脑里,这种恶劣的感情转化成对全人类的沸腾不息的恨意。
一次他很难得地去看他母亲时,他发泄了自己的愤怒,向接近她的那个男人猛掷了一个石块。
“要死了,你这小恶棍!”那个男人冒火了,“别找麻烦,你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吗。你以为是谁养活你的?”
男人走后,卫门又回到了客厅,凝视着他静默的母亲眩目的裸体。他摇摇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我想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每个人!)
这时阿千迎向他走去。
“我的儿子,试着去爱他们,”她喃喃,“你必须那样,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卫门感到震惊,他扑进她的怀里,紧紧依偎着她。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哭了,无法控制泪的泉水。
片刻之后,阿千结束了这段交流,她放开他,然后漫无目的地站在那里,那一刻卫门开始怀疑——希望!——她的疯狂也许只是一种完美的表演。但那也许可能只是混沌中闪过的一个清醒瞬间。没有迹象表明搅混了她意识的疯狂有一丝一毫的减轻。
卫门不太费神去深刻思考阿千的话,他对于人类的恨依然充满了心胸。但现在他拜访他母亲的次数大大增多了。几天后,或是几周后,他去拜访他母亲,当他坐在阿千身边的走廊上时,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个声音并不是在空气中传导的,也不是以形态或上下文的形式出现在他头脑里的。它是一个呼唤,仅仅对卫门一个人的——一种要把他拉到声音源头去的紧张感,就像抛出的绳索在往回拉扯。阿千俯瞰长长的河谷,她的脑海和平常一样空无一物。
“是谁呀?”卫门叫喊。
当卫门突然起身,喊出那个问题时,阿千转头去看他。她的脸,原本带着闲散空虚的神情,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