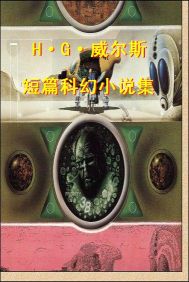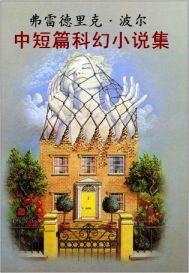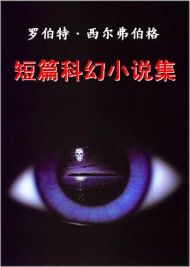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十一辑)-第18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我老了,力不从心了,有时摸索不到旋律了。音乐却对我不耐烦了。驱使着我,在我跟不上它的步伐时,掠走它赋予我的光芒。
当我像个垂死的人一样急需它的安抚时,它却变得冷若冰霜。
《折磨》作者:'日' 福田信孝
李重民 译
怎么回事!——
我对着镜子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吓得腿都变软了。
昨夜和同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回家时差一点儿赶不上末班公交车。酒喝到一半时脑袋里的意识就模模糊糊的,直到今天还酒气冲天,头一阵阵地疼痛。
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拧了一下自己的面颊,抹抹眼睛,都还有感觉。这绝对不是梦。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尽管不是做梦,却又完全像是一场噩梦。
“……我,我……成了我自己最最讨厌的芋山五平课长!……”
唉——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于是,镜子里的芋山也同样地躺下了。没错,现在的我就是芋山课长。
那个脑袋秃顶、大腹便便、脸和手都肥墩墩的、俗气的芋山课长,就是我的身影。
芋山课长今年45岁,口臭,爱盯着女职员的臀部看。我,我,为什么突然成了那个芋山课长!
真讨厌!——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沿着皱纹累累的松弛的皮肤流下。昨天以前我还是铃木一郎。那张童孩般的脸,胖乎乎的体型,虽算不上英俊,但还只有26岁,单身一人。那比这芋山不知要强多少。
我如此讨厌那个家伙(不,现在也许应该叫“我”),是因为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对我大发雷露。比如,我早晨一上班,这家伙就好像故意等着我似的,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身边。
“铃木,你还没有把报告写出来吗?傻瓜!”
“你不会写正规的计划书吗?笨蛋!”
“一看见你这张脸,我就会不称心·”
他用诸如此类的骂声向我扑来。如果是其他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决不会这么发火。
不知为何,这家伙把我当做他的眼中钉。所以,我对芋山课长讨厌得直冒胃酸。现在,我自己竟变成了那个令人恶心的人。
今后,我该怎么办……
我怔怔地发愣着。不一会儿,我想起一件事,便惊醒过来。
也许——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家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挤上轻轨列车和汽车,第一个跑进公司,来得比谁都早。
我在课长的座位上坐下,焦急地等待着上班的钤声响起。
不久,职员们陆陆续续地赶到公司里来上班,但里面没有我要寻找的人。到了上班的时间,有几个人奔跑着冲进办公室里,那家伙也在其中。
那人就是铃木一郎——昨天的我。
我死死地盯着另一个人的我。
年轻,虽算不上具有男子汉的气魄,但比这个芋山之类要年轻得多,长着一副不知辛劳的脸。上班的铃声已经响了,另一个我却还在和邻座上的女职员口若悬河地说着笑话。我不知为何,对昨天的自己感到非常羡慕。
我到底在干什么?——
竟然会有人像我成了芋山课长那样变成了我的身体?可是,那是谁?是芋山吗?还是……
我这么想着,脑子开始混乱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看就要发疯了,眼前的铃木一郎还在轻薄地和女人说着混账话吗?那张平静的、无忧无虑的脸。
我突然憎恨起那个家伙。我愤怒得连身体都抖瑟起来。
……我已经不能忍受!
我终于向那家伙发火了:“喂!铃木,过来一下!你在发什么牢骚!已经开始上班了!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你到底……”
《侦察》作者:克利福德·西马克
李志民 译
他的手表相当准,30年来分秒不差,是父亲遗留给他的。
今天他第一个来到编辑部,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才6点。再看自己的手表,竟已指着7点了,足足快了一个钟头。真不可思议!
的确,他来上班时,天都没亮,街上也几乎不见人影。
编辑部里也没有人,只有天花板上的两盏灯亮着。办公桌上电话机、打字机,外加一个白瓷浆糊缸统统挤在一堆。
眼下天黑人静,但再过一个小时一切就会活跃起来。新闻处处长艾德·莱因要7点半才来,采访部主任弗兰克·迈克也要随后才到。
他揉了揉眼,显然睡意未消。本来他还可以再睡一个钟头的……
可别怪表!事实上他今早并不是按表指的时间起的床,而是被闹钟吵醒的。闹钟也整整快了一个钟头。
“真是怪事!”他大声说着,走向自己的工作台。突然他发现打字机旁有个东西在动,那东西形如老鼠,发出金属光泽,亮锃锃的,仿佛还有一种魔力。他犹如生了根似的提不起脚来,喉咙发干,心口烦闷。
这奇怪的东西端坐在打字机旁,死盯着他。尽管它没有眼睛,没有嘴巴,但他确有一种老被它盯着的感觉。
他伸手去拿白瓷缸。浆糊怎么能乱放呢!可瓷缸却抢先紧随那怪物躲开,向桌边滑去。忽听哐当一声,它跌落在地,摔得碎片四处乱飞,黏糊糊的东西撒了一地。
那锃亮的东西头朝下裁倒在地,爪子磕得叮当响,但它马上又翻身而起,迅速逃窜。
他气愤之极,摸到一根铁棍,顺手掷了过去。铁棒落在那家伙的鼻尖前,戳进了地板,溅起少许木屑。
铁鼠吓得往后一退,马上灰溜溜地钻进壁柜门缝里去。壁柜里放着墨水、纸张和其它办公用品。
他赶上去,用手往柜门上一拍。嗒的一声,门关上了。
他背靠柜子,仔细一想,不免心里发毛,甚至有些害怕。那鼠样的东西,或许就真的是一只老鼠,一只银鼠。
但它却没有尾巴,也没有嘴,而且老是盯着我看。
他自言自语说着,离开了柜子。佐·克雷因呀,你可是神经出问题了?
这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1962年10月18日清晨的此时此刻,不可能发生在20世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
他转过身去,抓住门把手,想把门打开。可把手不听使唤,门怎么也打不开。
他心想:门怕是在我拍打的时候,无意中给锁上了。我没有钥匙,钥匙在朵罗蒂那里。但是,她一向都是让这个柜子开着的,因为那把锁有问题,一旦锁上,就很难打开。她常常不得不去请门卫来帮忙,或许,我也得去请门卫或钳工来?我这就去请,把情况说清……
可说什么呢?说我看到一只铁鼠钻进柜子里去了吗?还有,铁棒还插在房中央地板上呢!
克雷因摇了摇头。
他走过去把铁棒拔出,放回原处,又收拾了一下瓷器碎片、木屑和浆糊。这才回到桌前,取出三张白纸和一张复写纸,并把它们装到打字机上。
谁知,他连键都还没触到,打字机就自动打起字来。他惊呆了,定定地坐着,看着。机头在来回移动着,很快就打出一条字来:
别乱来,佐。别把事弄糟了。否则你会倒霉的。
佐·克雷因把纸抽出,揉做一团,扔进字纸篓,然后到小吃店喝咖啡去了。
“您知道,鲁依,”他对店老板说,“当你孤身一人在家时,你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对呀,”鲁依附和说,“我要处在您的情况下,早就发疯了。既然您在您屋里感到苦闷、空虚,甚或害怕,那您最好马上把房子卖了。那房子就像一个死去的老太婆,留有何用,马上卖了吧。”
“我不能卖!”克雷因语气坚定,“它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那您就娶个老婆吧。”鲁依劝道,“您老是单身过日子总不好嘛。”
“现在已为时过晚。”克雷因说,“请别为我操这份心了。”
“哎,我还藏着一瓶陈酒呢。我不能就这么亏待您,真不该啊。要不,我在咖啡里给您倒上一点?”
克雷因摇了摇头。“不了,我马上就要干活去了。”
“真的不想要?我可不是为了赚钱,纯粹只是为了友谊啊。”
“不了,谢谢,鲁依。”
“也许,您现在也产生了幻觉吧?”
“幻觉?”
“是的。您刚才说过,当您孤独时,你会产生幻觉。”
“这话我说过,不过,那是为了用词高雅而已。”克雷因解释说。
他很快喝完咖啡,回到编辑部。
现在一切都已正常。艾德·莱因在训斥着某人,弗兰克·迈克在删改竞赛报晨版号外。来了两名采访记者。
克雷因斜起眼睛偷偷地看了壁柜一眼,柜门仍旧紧闭着。
采访部主任办公桌上电话响了。主任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把话筒移开,用手捂住送话器,不让对方听到他下面的话。
“佐,”他喊道,“您来接。有个疯子坚持说,他好像看到一台缝纫机自己会在街上跑。”
克雷因取下自己的电话。
“请把245号转给我。”他向接线员请求。
“是盖拉德吗?”对方先问,“喂,是盖拉德吗?”
“我是克雷因。”佐说。
“我要找盖拉德。”听筒里重复着,“我要跟他通话……”
“我是《盖拉德》报社编辑部的克雷因。有话请讲。”
“您是采访记者吗?”
“是的。”
“那么请听着,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我在街上行走时,看见……”
“在哪条街?”克雷因打断对方,“您贵姓?”
“在莱克…斯特里街。”对方答,“是在500号,还是在600号门口,我记不清了。我正走着,迎面突然滑来一台缝纫机。我想,准是谁丢失的,可仔细一看,街上什么人也没有。这条街很平,一点坡度也没有,它是在自己溜啊……”
“您贵姓?”克雷因插问。
“姓名吗?我叫斯米特,吉弗·斯米特。我想应当帮一帮丢失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