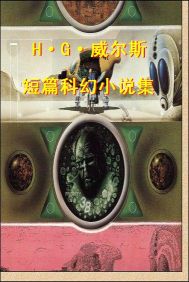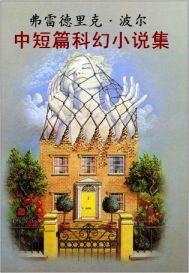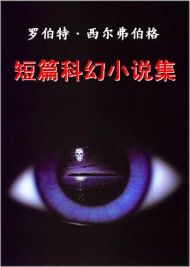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七辑)-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彭布列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丹尼尔·塔里亚:
学生的这个提案对教师不适用,但显而易见,如果提案通过了,那么教师也面临安审美干扰镜的压力。所以,现在就表明我的态度并不操之过急,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
这是“政治正确性”胡作非为的最新例子。提倡审美干扰镜的人用心是良好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在把我们当作幼儿对待。认为美是我们需要避而远之的观点简直是在侮辱人。要知道,下一步某个学生组织就会坚持要我们所有人都安上音乐审美干扰,这样当我们听见天才的歌手或者音乐家演唱时,就不会自惭形秽了。
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竞技,你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吗?当然不会。相反,你只会感到惊叹与羡慕;你会为有如此杰出的运动健儿存在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么,对美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同样的感受呢?女权主义会要求我们对这个反应做出道歉的。它想用政治取代审美,而且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就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的人性沦为贫困。
待在一个世界一流的美人跟前犹如聆听一首女高音歌曲,令人销魂。并非只有天才才从他们自己的天赋那里获益,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益。或者,应该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剥夺我们这种机会可是作孽呀。
“支持合乎伦理医药人民组织”打的广告:
画外音:你的朋友一再告诉你说,审美干扰镜很酷,安上爽极了,对吗?那么,也许你应该找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人谈一谈。
“我关闭审美干扰镜之后,第一次见到相貌平庸的人就忍不住退缩。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但还是忍不住。审美干扰镜并没有帮助我成熟,反倒阻止我成熟。我还得学习如何同人相处。”
“我上大学学习平面造型艺术。我不分白天晚上地刻苦用功,可是一点长进也没有。老师说我缺乏艺术眼光,就是那个审美干扰镜阻碍了我的审美趣味发展。我失去的东西没法找回来了。”
“安着审美干扰镜的感觉就好像我的父母待在我的脑子里,审查我的思想。现在我把它关闭了,这才恍然大悟:我是在什么样的虐待中长大的。”
画外音:如果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人并不推荐这东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年他们没有选择,而现在你却可以选择。不管你的朋友说什么,损伤大脑绝不是什么好事。
玛丽亚·德苏扎: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支持合乎伦理医药人民组织”,因此对它进行了凋查。我们费了一番功夫去挖掘,结果表明它压根儿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企业公共关系联盟。一些化妆品公司最近聚在一块,共同建立了这个联盟。至于出现在广告里的人,我们一直没能够同他们接触,因此他们的话即使有真实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可信度。即使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自身也肯定没有代表性。大多数关闭审美干扰镜的人都感觉良好,而且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的平面造型艺术家肯定是有的。
这多少使我想起不久前我看到的一则广告,广告是由一家模特代理打的,当时审美干扰镜运动才刚刚开展。广告只是一张一个超级模特面部的图片,上面有一个标题:《如果你无缘再见她这么楚楚动人,那是谁的损失?她的还是你的?》这场新的宣传攻势表达的是相同的信息,大概是说:“你会遗憾的。”只是它没有带着趾高气扬的语气,而是更多地装着关心警示的口吻。这就是经典的公共关系策略:躲藏在一个动听的名字后面,给人以替消费者利益说话的第三方的印象。
塔玛娜·莱昂斯:
我认为那则商业广告愚蠢透了。这并不是说我赞同提案——我不希望人们投票支持——但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理由投票反对。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并不会带来严重的伤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我什么的感到遗憾,我处理得很好。所以说,我觉得人们应该投票反对审美干扰镜,是因为看见美丽挺惬意的。
不管怎样,我又跟加雷特谈了一次。他说他刚刚关闭审美干扰镜不久。他说到目前为止,他的感觉似乎很爽,只是有点离奇。我告诉他说,我关闭审美干扰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关闭审美干扰镜才几个星期,但却仿佛在扮演一个老资格的赞成关闭审美干扰镜的角色似的,想起来真有点滑稽。
约瑟福·魏因加藤:
关于审美干扰镜,研究人员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有任何“副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否影响你对除了相貌之外的美的欣赏。对于大部分事物来是,答案似乎是“没有”。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欣赏的东西似乎与其他人相同。就上述而言,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有副作用的可能。
例如,就拿在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人身上观察到的副作用说吧。有一位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是个饲养奶牛的农民,他发现他再也不能一头一头地辨认他的奶牛了。另一位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人现在比以前更难区分小车的型号了。这些是可以想像的。这些例子说明,除了辨认面孔的严格范围之外,有时候我们还用面孔辨认模型来辨认别的事物。也许我们不会认为某个东西——比如一辆小车——看上去像一张脸,但在神经病学的层面上,我们却把它看作仿佛是一张脸。
在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中间也可能存在相似的副作用,但由于审美干扰镜比相貌识别干扰仪更精微,因此任何副作用都更难以测试。譬如,时尚在小车外表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在人的相貌方面,因此对于哪些小车最有魅力,可能没有一致的看法。也许有的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对于某些小车的欣赏程度不如他们没安审美干扰镜的时候,但还不至于到了抱怨的程度。
接下来,还有我们辨认美的模型在我们对对称的审美反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广阔的背景范围里欣赏对称——绘画、雕塑、平面艺术造型——但同时我们也欣赏不对称。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涉及诸多因素,但在什么时候某个具体的事例子是成功的,对此却没有一致的看法。
了解安有审美干扰镜的群体是否更少产生才华横溢的视觉艺术家,也许是有趣的,但由于人民大众中所产生的天才艺术家本来就寥若晨星,因此很难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只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据报道,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对某些肖像画的反应要微弱些,但这不是副作用:肖像画的魅力至少部分来自画中人的相貌。
当然,有些人对效应十分敏感。这就是有些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安审美干扰镜的理由: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欣赏蒙娜·丽莎画像,也许还能够继承肖像画的传统呢。
沃特斯顿学院四年级学生马克·埃斯波西托:
彭布列顿大学事件听起来真是荒唐绝顶。我看好像有意戏耍人似的。比方说,你安排这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见面,你告诉他她绝对是个漂亮小妞,但实际上你却给他安排了一条狗,而他由于过于相信你,因此认不出来。真有点滑稽。
不过,我肯定永远不会安审美干扰镜这东西。我想和漂亮小妞耍朋友。我干吗要降低自己的标准,随便将就呢?当然,有些个晚上漂亮小妞全给选走了,你只好挑残羹剩菜。所以说酒吧里才会有啤酒,没小妞时只能喝喝啤酒了,对吧?是不是说以后我也得弄副啤酒干扰仪戴戴。
塔玛娜·莱昂斯:
昨天晚上我又和加雷特在电话上聊天。我问他是否想转入视频交谈,这样可彼此看见对方。他说好的,于是我们就转入了视频。
我随便准备了一下,但实际上花费了不少时间。琳娜在教我化妆,但我在这方面不在行,于是我就使用一种耳塞式软件,可以使你看起来好像化了妆似的。我稍稍调了一下软件,于是我想我的形象就大不一样了。也许我做得过分了,不知道加雷特能够看出几分来,但我只想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地好看。
我们一转入视频,我就看出了他的反应。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好像说了句,“你显得真漂亮,”我好像也说了句,“谢谢”。接着他害羞起来,对自己的模样开了些玩笑,我告诉他我喜欢他的形象。
我们在视频上聊了一阵,我感觉他一直在望着我。那种感觉真好。我有一种感觉:他心里在思考是否应该和我重新相爱,但这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也许下一次通电话,我要提议周末他来看我,或者我上诺思洛普去看他。那才爽呢。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学会化妆才行。
我知道不能保证他重新回到我身边。我关闭审美干扰镜,并没有减弱对他的爱,但也可能使他不再爱我了。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
三年级学生凯瑟·米纳米:
谁说审美干扰镜对妇女有好处,谁就是在为所有压迫者的宣传摇唇鼓舌:把征服说成保护。审美干扰镜的支持者们将拥有美丽的女人妖魔化。美不仅可以向拥有美的人提供愉悦,也可以向接受美的人提供同样多的愉悦。可是审美干扰镜运动却偏偏使妇女对从自己的容貌中获得愉悦而感到负疚。这是男权社会压抑女性美的又一策略,这次偏偏又有太多的妇女出钱加入进去。
当然,美一直被用作压迫的工具,但消灭美并不是答案。你不能通过缩小人们的外表差异来解放他们。这简直就是奥威尔④小说中所描写的非人性压迫。真正需要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审美观,让所有妇女对自己感觉良好,而不是使大多数妇女感觉糟糕。
四年纪学生劳伦斯·萨顿:
我对沃特·兰伯特在演讲中所谈的东西了如指掌。我不会用和他相同的词语来表达,但有好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却是一样的。我是在几年前安上审美干扰镜的,早在提案之前,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