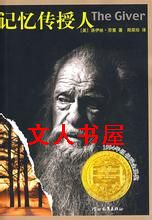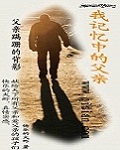记忆碎片 :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到宾馆,在自己的房间洗完澡,然后他敲响了她的房门。她开门,放他进来。她也已经洗过,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的。他们分别坐在两张床边,聊着天。他频繁地用眼瞄她,她裸露在睡衣外的肌肤泛着一种光洁的色泽,一笑起来,脚弯成一种很动人的弧度。用句鸳鸯蝴蝶的笔法吧——他的心弦拨动着幸福的颤音。
终于,夜深了,终于,她在看表了。他站起身来要走,她也站起身来送他。他一下子抱着她,用一个想象了千百次的动作。她挣了一下,然后也环抱住他。
进展到这里,情节还跟他设想的一样,但就在她回抱他的那一刹那,他顿时头晕目眩,原本设计的迫不及待地撕扯对方衣服的程序也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是和她拥抱在那里,两人均一言不发,时间过了那么长,那么长,他觉得她比他还小,让他怜惜,他觉得自己拥有的幸福足以傲视整个世界,他觉得地毯柔软,灯光温柔。
他凑过去亲她,手也开始摸索,但都被她身体的扭动制止了。她说:“你该回去了。”他说:“让我不走吧。”她摇摇头。
“好吧。”他亲了一下她的脸,离开她的房间。
接下来在无锡的几天,他和她看了锡惠山的杜鹃花,饱览了太湖秀色,在灵山大佛前许了愿,寻找段誉和乔峰“剧饮千杯男儿事”的松鹤楼未果,晚上到了宾馆,他仍是洗过澡后去她的房间,聊天,欣赏她的身体,起身告别时拥抱在一起,求她别让他走,灰溜溜地回自己房间。
如果他再坚持一下,如果他用些蛮力,如果他的脸皮再厚些……但是,没有如果。那些情色、色情小说的作者,那些情色、色情电影的导演,他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泡过妞,或者,他们是用虚构的热辣场面来弥补自己的失败?他将那些人的三代直系女眷问候了一遍,以消解自己被误导的性爱方式。
他只能让自己独自上床,脸上带着空落落的笑意。而那些被他惦记着扯坏的衣服,全都得以保全。
离开无锡后,他和她坐在火车上,他悄悄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渐渐变得温热。他不知道自己的心中是满足还是缺失,是幸福还是痛楚?
日子继续一天天地过去,杨蒜苗和黄红梅仍然像从前一样,同事。只是在没有旁人的时候,蒜苗才用渴慕的眼神看着黄红梅,身体依然是不动声色。
只是在那一个夜晚,他第一次为她流泪,尽管这世界上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泪水是为了谁。
康乃馨要去新加坡工作,那天是大家为她饯行,喝得不亦乐乎,包括黄红梅一家三口。耳花眼热后,意气素霓生,大家又去歌厅卡拉OK。在酒精的作用下,杨蒜苗的眼神变得像蒜苗一样火辣辣,也狂放起来,和黄红梅的儿子争夺着话筒。最终,他向大家展露了一手深藏不露的手艺:居然会唱京剧,铜锤花脸。
他唱的是《铡美案》中的一段散板。民女秦香莲被她丈夫的公主二奶和皇帝的老婆宣召上堂,她哪儿见过这等世面?包拯便拍着胸脯唱了几句来为她鼓劲,特别是最后一句“天塌地陷有老包”,格外声情并茂,浑厚悠长。康乃馨明显被感动了,动情地搂住他的肩头,当作是他的临别决心。而他,却借着酒劲痴痴地看着黄红梅,想到她正在为老公的婚外恋伤心,想到她还要努力装作生活圆满的样子,想到她正遭到与她竞聘副总经理的男人排挤。“天塌地陷有老包”,这句话让他豪情万丈。我会和你在一起,不让你受委屈。他心里在说,又痛又怜,眼中有泪光闪动。
“唱得真有气势。”黄红梅攥着儿子的手鼓掌,然后对康乃馨说,“我还老想他是当年那个小伙子的样子,其实人家都是个大男人了,让人靠得住。”
康乃馨骄傲地看着蒜苗。
妻子走了,日子继续一天天地过去。
经过康乃馨两年的艰苦打拼,杨蒜苗也可以移民新加坡了。他来北京办签证的时候,黄红梅正巧也在北京,给在医院治病的老母亲陪床。
接到他的电话,黄红梅马上从医院跑了出来,两人得以在北京相聚。
“那里还好吧?”饭桌上沉默了许久,她才问他。其实这个问题她早就问过了,在他去新加坡探过一次亲之后。
“还好吧,我对那个规规矩矩的国家很是喜欢,也喜欢河以南的‘老巴刹’,跟咱们的大排档一样,全是各种好吃的。”他答道,也跟以前的答案一样。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哦,用新加坡式华语,‘不知道’要说‘不懂’。”他笑着说。
“好吧,我不懂你。”
他的心颤了一下。
吃过饭,他和她坐上一辆出租车,先奔向他住的宾馆。他产生了一个淡淡的想法,希望能和她有最后一夜。到了宾馆,她却要接着走,说母亲还在医院。他握住她的手,扭头看她,脸色劳顿。他和她一起来到医院,看了她的母亲。
他执意让她去宾馆住一晚,他来陪床。两人又打车,他送她回宾馆。
他领她进了房间,然后要返回医院。
两人的眼光交织在一起。他摊开手,她走过来,贴在他身上。他合上双手,将她拥在怀里,爱抚着她几天没洗的头发。
他突然想到,她原来已经四十二岁了。
你的故事讲到这里,看到见招拆招脸上挂了两行泪。
杨蒜苗然后去了医院,陪了一夜床,等到第二天上午,黄红梅来接他的班。然后,他就去了新加坡。两个人的肉体接触,就以在无锡的一个拥抱为起点,在北京的拥抱为终点,故事就是这样。
如果让你们这些文人来写,这肯定是个凄凉的调子,但我看蒜苗和红梅都挺开心的。这世界很不公平,大家都在泡妞,却只有文人的泡妞历程才被记录下来,并且因为文人那种得蜀望陇的不知足心理,所以还总带有深深的怨妇情结,好像谁都对不起他似的。
见招拆招长出了一口气,不再反驳你。
杨蒜苗跟我说起他的故事的时候,是那种很幸福又留恋的神情,天高云淡。他在那个单位上了十五年班,也就是和黄红梅在一起待了十五年。他舍不得迟到、早退、旷工,因为爱黄红梅而成了劳模,大概黄红梅也是吧。一个人每天醒着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十来个小时,而在这十几个小时中,他却有八个多小时和她在一起;一个人生命的黄金岁月也就是二三十年,他却有十五年的时间和她在一起——老天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这不应该是个忧伤的故事,你看你都没出息地哭了,真让俺鄙视你。
我想起我心爱的姑娘曾经问,你痛苦吗?
有一个人可以喜欢,怎么会痛苦呢?
行为艺术
两瓶二锅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干掉,这时不到凌晨三点,你和见招拆招酒兴大发,都不想就此打住。见招拆招去厨房翻箱倒柜,试图挖掘出珍藏的陈酒。
泰戈尔说:“天空中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曾经飞过。”
“我从天空中飞过,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悲观主义者将这两句诗颠倒了一下,以抒
胸臆。
在泡妞这桩行为艺术上,你是泰戈尔,还是悲歌尔?你喃喃地说。
见招拆招终于翻出一瓶酒,重新归位,将其打开。我发现泡妞就像烤红薯,吃着不如闻着香。至少写起来,泡不着的泡妞过程更好看。或者,我们现在老了。年轻时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现在却成了“重要的是参与”;年轻时的泡妞奥运会恨不得一年开四届,现在能四年开一届就不错了。
重要的是参与,重要的是过程,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你说。
见招拆招点头称是。就像我们看的那些电影,一个女孩险些被一个歹徒强迫上了床,幸有英雄救美,最后女孩就跟英雄上了床。早知道是这个结局,还不如一开始就从了。
但真不能这样说,泡妞嘛,一定要把过程弄得患得患失些,若即若离些。要不,岂不是太不好玩了?其实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在中间那个过程上玩花样,并且看谁玩得有趣,玩得新鲜。
好吧,那就让我们说点儿不太伤感的泡不着的故事,缓和一下被你这头猪弄得抑郁起来的气氛。见招拆招说。
近水楼台先得月,世上的泡妞千万种,却只有作家们的泡妞被讴歌得最多。其中最常见的段落——至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段落是,某作家在火车上,邻座有个美丽的女孩,丁香一样结着愁怨,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是这位作家的大作。作家与那女孩做一席谈,帮助那女孩鼓起生活的风帆,最后那女孩会给他留一个写着地址、电话、mail、QQ号和个人主页的纸条,两人从此就搭鼓上了。
孙冬瓜对这样的泡妞方式充满艳羡,因为,其一,尽管他不是个作家,但也算是个记者,这年头记者出的书比作家都多;其二,他经常坐火车出差采访,有充足的平台让他结识那些丁香姑娘。
但说来奇怪,他坐火车无数次,邻座及对座却全是散发着汗臭、打开一袋花生米和一瓶桔子罐头,然后用粗大的手指顶开一瓶啤酒的男人,留着猪鬃一样的胡子。只要他用眼一瞟,对方的话就会紧紧跟进,与他称兄道弟起来。每次坐火车,都是这样。他一方面怀疑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因为满腔的春心得不到发泄,而让自己结了一身丁香般的愁怨。
命运终于等到了转机。这次,孙冬瓜由北京去上海出差,往返于两个中国最繁华时髦的都市,怎么着也得换换手气吧。
果然不错,从北京去上海的火车上,孙冬瓜的身边是一位老太太。
孙冬瓜已经很满意了。老太太就老太太吧,他坐火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跟一位异性比邻而坐。
采访结束后,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孙冬瓜这次长了个心眼,委托《新民晚报》的朋友给买了张软卧车票。单独一个车厢,一位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