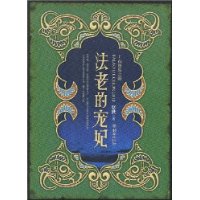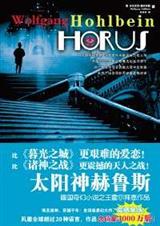为普鲁斯特哭泣-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攘丝谄【疲穆庾愕胤畔拢瓢勺抛臁M忌嬲棺哦钔罚劬ο褚估且谎秸鲈酱螅痪帽憧忌⒎⒊鲇睦兜墓饷ⅰG浊祝颐蔷倨鹁票�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在《先生》中,“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照相机》中的主角也没有名字,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体味着自己的无所作为。我发觉自己的生活——至少是一部分——和图森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相像。图森小说主人公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困境,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准确的概括和预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森小说的普遍性。图森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大师,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仍然是稀缺的。
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溜溜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长的影子。这串影子中最突兀的是图森。他脚步迟缓,目光飘忽,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的脚步和目光从来不在同一个事物面前长久地停留。导游不懂英语,杨一用一种混杂着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的拙劣语句向图森解说着。图森礼貌地点着头,一副完全听懂的样子。
鲁迅祖居的屋顶像一顶官帽。会客厅的太师椅透着威严。房间走了一间又一间,好像没有尽头。卧室里的床也是黑色的,床上整齐地叠着红色的被子,好像刚刚有人睡过。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压抑的地方。图森从这些地方快步走过,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对中国传统的感受,图森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就出了门。
鲁迅祖居门口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老人。我们一窝蜂涌过去,臭豆腐顿时脱销。一部分人先吃,吃完了去参观马路对面的三味书屋。另一部分人等在油锅边,边炸边吃。那边去参观的人都回来了,这边还有人在等臭豆腐。图森抹了抹吃得很油的嘴。
从青藤书屋出来,我们继续走在那条狭窄的弄堂里。弄堂两侧有很多发廊,里边的小姐笑容暖昧。Hello,小姐叫道。图森居然从一开始就不加理会。头顶的天空拉满了电线,晾满了女人的衣服,正在往下滴着水,图森一律视而不见。在另一条弄堂入口处的墙上,写着硕大的“浴室”两字,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标着“厕所WC”字样。浴室,浴室,我们叫道。这回图森听见了。我们示意他在“浴室”两个大字旁边留个影,他欣然同意,并且摆出一副举着相机拍照的姿势。这幅照片将只有一个名字:浴室·先生·照相机。我们在给图森拍照的时候,路边糕点店的伙计说:“和厕所拍照,哈哈。”我们这才发现那两个大字写在一座厕所的墙上。
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凄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系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溜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溜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溜冰场上。溜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征,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溜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