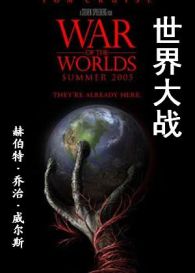102世界大战 [美] h·g·威尔斯-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这种声音没有音调的调整,在我看来,只是在注射前舒一口气罢了。我自认为有些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我非常有把握地相信,就象我相信其他的事情一样——火星人可以不通过说话这种物理方式交流思想。我虽然曾对此颇有成见,但仍然深信不疑。有些读者大概记得,在火星人入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对心灵感应作过相当激烈的批驳。
火星人不穿衣服。出于需要的原因,他们对装饰和礼节的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不象我们对温度的变化那样敏感,而压力的变化对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很严重的影响。虽然他们不穿衣服,但身上仍然佩带一些人工制成品,这使他们比我们更为优越。我们拥有自行车、溜冰鞋、大炮和刺刀诸如此类的东西,但这只是火星人业已完成的演化进程的开端罢了。他们几乎完全变成了大脑,根据各种需要穿着不同的外壳,就像人类穿上西装,骑上自行车赶路,或者在下雨的时候打伞一样。至于他们的各种装置,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缺乏所有人类机械的主要特点——没有轮子——他们带到地球上来的所有东西找不到使用轮子的一点痕迹。人们猜想至少要使用轮子运动吧。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地球的自然环境里从来就没有产生轮子的概念,而是发展出了其他的替代方式。火星人不仅不知道(真是难以置信),或者不愿意使用轮子,而且他们的机械装置里不使用固定的和半固定的轴心,因为圆周形的运动会把它们限定在一个平面里。机械的所有关节由滑动部件构成的复杂系统构成,这些部件在小小的,具有非常幽雅弧线的摩擦轴承上活动。关于这个细节,我得指出,他们机器里的长连杆大部分是由象筋肉组织一样的圆盘连接起来的,这个圆盘给包在有弹性的套里;当电流通过时,这些圆盘就被极化,紧紧地拉在了一起。用这样的方式,这些机械获得了和动物一样灵活的运动方式,这使看到它们的人感到非常吃惊。在螃蟹似的修理机里有许多这样类似肌肉的组织,我第一次从裂口里看到打开的圆筒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它看起来比躺在一边的火星人更有活力。经过了穿越太空的旅程之后,火星人在夕阳底下喘着粗气,活动着不怎么灵活的触角,有气无力地爬动着。
当我还在看着火星人在阳光下缓慢的动作,注意着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牧师用力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才想起来他的存在。我回过头,看见他忧郁的脸和紧闭的嘴唇。他也从开口里张望一下,因为开口只能容下一个人观察;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观察,让牧师享受一下他的特权。
我再看的时候,那架忙碌的修理机已经把圆筒里的几个装置拖出来,组成了一个和它自己外形相象的机器;在左下方露出了一个挖土机器,一边放出绿色的烟雾,一边在大坑的边上工作着,有条不紊地把土挖出来,然后压平。它发出了锤击声和有规律的震动,让我们藏身的房子也抖动了起来。它一面挖土,一面喷着烟,发出哨声。就我所见,这个机器没有火星人在操作。
《世界大战》作者:'美' H·G·威尔斯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三章 被困的日子
第二个战斗机器把我们从窥视的开口赶到了储藏室里,因为我们害怕火星人能从高处看到我们。后来几天我们觉得危险少了一些,因为在外头的阳光下看来,我们的隐蔽处一定是一片漆黑,但是一有了火星人接近的动向,我们就立即撤回储藏室里去了。虽然我们的观察非常危险,但我们两个人都无法抵御这个诱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让我惊奇的是,虽然我们身处绝境,很可能饿死或者给杀死,为了获得观察火星人这个可怕的优先权,我们仍然激烈地争吵着。我们在厨房里相互追逐,充满敌意,却又怕弄出响声,我们就这样拳打脚踢,有时离暴露只差一点。
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和习惯以及行为完全不同,我们的危险境地和隔绝状态更使这种隔阂有增无减。我在哈利伏特的时候,早已经开始对牧师这种无助呓语的把戏和愚蠢的固执己见感到憎恶。他无休止的自言自语让我没有办法想出任何的行动方案,他的行为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简直快要给他逼疯了。他象一个愚蠢的女人一样缺乏自制力。他能连续不停地哭上几个小时,我深信这个象给惯坏了的小孩子一样的家伙相信,他的眼泪几乎是一种灵丹妙药。我有时在黑暗里坐着,脑子里根本无法摆脱他没完没了的絮叨。他吃得比我还多,我枉费心机地想让他明白,我们逃生的唯一希望是等在房子里,等着火星人完成在土坑旁边的工作。在这样的漫长等待当中,我们肯定会需要食物。他却不能控制自己,连吃带喝,他睡得也很少。
随着一天一天过去,由于牧师对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做任何打算,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我虽然很不愿意这么做,但不得不开始对他采取威胁的手段,到了最后甚至不得不打他了。这让他脑子清醒了一段时间。但他是属于那种脆弱的人,没有自尊心、畏惧、卑贱,专门施展狡猾的伎俩,对上帝,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要撒谎。
我写的这些确实不令人愉快,可是我这么做只是想让我的故事完整一些。生活中从没有过黑暗和可怕经历的人,一定会责备我对我们这个悲剧故事充满残忍和愤怒的描写;因为他们知道明辨是非,但是却不知道受尽折磨的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但是那些曾经生活在阴影底下,饱尝了千辛万苦的人,是会更容易理解我的。
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压低着声音相互责骂,争抢食物和饮水,一边打打闹闹,外面,在六月灼热的阳光下,是一幅怪异的景象,火星人在坑边进行着不为我们熟知的工作。让我再说说自己的第一印象吧。过了很久,我回到了裂口处,发现三个战斗机器加入了新来的火星人。这些战斗机器带来了一些新的装置,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圆筒的外面。第二台修理机已经组装好了,正在战斗机器带来的一个新装置的旁边忙来忙去。这个装置象一个牛奶壶,上面有一个振动的梨形容器,从容器里流出一些白粉,撒在底下一个圆形的盆子里。
振动是由修理机的一个触手产生的。只见修理机发出一阵微弱的,音乐般的金属撞击声,象拉开的望远镜筒一样伸出了一个触手,这个触手原来只是一根突出的短棒,现在短棒的一头已经伸到了土堆的后面。又过了一会儿,这个触手向上举起一根闪闪发亮的白色铝棒,把它和坑边的一堆铝棒放在一起。在从日落到星星升起的这一段时间里,这架灵巧的机器已经用土制成了不下一百条这样的铝棒,蓝色的灰土一直堆到了大坑的边缘。
这架动作灵活,结构复杂的机器和那些行动笨拙,气喘吁吁的火星人的对比是那么的强烈,以致于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那些火星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生物。
第一个人给带到坑里的时候,牧师正在缺口边观察。我坐在下边,弓着腰,用心地听着。他突然朝后一退,我害怕给火星人发现,不由自主地缩起了身子。他在黑暗中从垃圾堆上爬下来,来到我的身边,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一边打着手势。有那么一会儿,我也有些惊慌失措。他的手势是叫我到裂口处看一看,过了一会儿,我的好奇心让我来了勇气,于是站起身,从牧师的身上跨过去,爬到了裂口的边上。起先,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让他那么恐惧,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星星又小又暗,可是土坑却给制造铝棒时闪耀的绿色火光照得很亮。我的面前是一副由绿色闪光和黑色影子构成的影象,看上去非常奇怪。在这副画面的后面,飞着几只蝙蝠,它们完全不理会所发生的一切。火星人已经看不见了,它们给升起的蓝绿色的灰土挡在了后面。而战斗机器则把腿缩短了,蹲在坑的旁边。后来,从机器的轰响之中,飘过来好象是人的声音,我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
我蹲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战斗机器,头一次发现了待在头罩里的火星人。当绿色的火光升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它的油光发亮的外皮和闪光的眼睛。突然我听见一声大叫,看到一个长长的触手伸向了安放在后背的一个笼子。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挣扎着的什么东西给高高举了起来,这个模糊的黑色影子给映照在星光下;那是一个体态粗短、健康的中年人,他的穿着很讲究;三天以前,他一定还是世上的一个名人。我能看见他睁大的眼睛和钮扣和表链上的闪光。他在土堆后头消失了,一切又安静了下来。然后就传来了哀号声和火星人的欢呼声。
我从垃圾堆上滑下来,慢慢站起身子,用手捂住耳朵,向储藏室奔去。牧师静静地蹲在地上,用两个胳膊抱着头,看见我跑过去的时候,他一边大声地责骂着我抛弃了他,一边跟了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藏在储藏室里,时而感到惊恐不安,时而又想着我们看到的景象,虽然我觉得有必要马上采取行动,但是却想不出逃跑的计划;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开始情形地考虑我们的处境了。我发现根本没法和牧师商量任何事情,他给我们不断恶化的状况吓得惊惶失措,已经完全丧失了明辨事理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为将来打算了。他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了一个野兽的地步。但是我却从不放弃任何希望。一旦我面临事实,我越来越相信,虽然我们处境很可怕,但还没有到彻底绝望的地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火星人只把大坑当作临时驻地。即便它们把它当作永久性的驻地也无妨,因为火星人不一定认为有看守土坑的必要,这样,我们还是会有机会逃跑的。我甚至还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