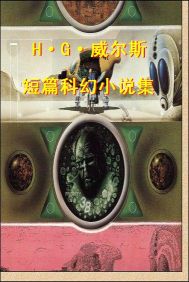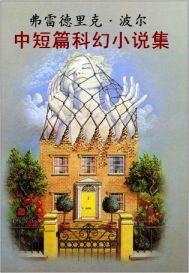218 科幻之路 第三卷-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我们走了,又飞上天。
我们降落在休斯敦:
“该死的!”缪斯说。“双子座航班调控站——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咱离开这里,请吧!”
我们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出发了,经过帕萨迪纳,随后沿单行道到加尔维斯顿,打算乘这部公共汽车到加勒比海湾,但是洛见到一对夫妇开着一辆载客的卡车——
“很高兴让你们搭车,太空人。你们这些人在行星和那些劳什子上面,为政府干了不起的工作嘛。”
他们带着婴儿,要到南方去,因此我们坐在车后部,一路风吹日晒颠簸了二百五十英里。
“你想他们是太空情种吗?”洛用胳膊肘捅捅我问道。“我敢打赌他们是太空情种。他们正等着我们去勾引呢。”
“住嘴。他们只不过是一对好心肠的乡下蠢娃娃罢了。”
“这可不能说明他们不是太空情种!”
“你对谁也不信任,对吧?”
“没错。”
最后我们又搭上一辆公共汽车,一路嘎吱嘎吱穿过布朗斯维尔,车子在飞扬的尘土中下了台阶,进入炎热的傍晚,然后驶过边界进入马塔莫罗斯,在那儿我们惊动了许多墨西哥人、鸡鸭和得克萨斯海湾的捕虾渔民——他们身上臭气薰天——我们叫得最响。四十三个妓女——我数过——浩浩荡荡出来迎接捕虾渔民,我们打破公共汽车站的两扇窗子,她们全都放声大笑。捕虾渔民说他们不买东西给我们吃,但是假如我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灌个烂醉,因为这是捕虾渔民的风俗习惯。但是我们吼叫着,又打破了一扇窗户;随后,当我仰卧在电报局阶梯上哼唱的时候,一个黑嘴唇的女人弯下腰,双手捧着我的脸颊畸“你真可爱。”她那粗糙的头发垂到面前。“但是那些个男人们,他们站在四周围观着你呢。这就占用时间了。挺遗憾的,男人的时间就是女人的金钱。太空人,难道你不认为你们这些……人应该离开吗?”
我抓住她的手腕。“你!”我悄悄地说。“你是太空情种吗?”
“太空情种在西班牙呢。”她笑容可掬,拍拍我裤腰带扣上的旭日形饰针。“对不起。但是你压根儿没有……对我有用的玩艺儿。太遗憾了,因为你这模样好像过去是个女人身,不是吗?我也喜欢娘们……”
我从走廊台阶上滚落下来。
“到底是这个拖后腿还是这个拖后腿!”缪斯大嚷大叫起来。“得啦!咱走吧!”
我们总算在黎明前回到休斯敦。回到太空。
我们降落在伊斯坦布尔:
为巧天早晨伊斯坦布尔下看雨。
在一处自动售货店里我们喝着梨形玻璃杯里的茶,眺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王子群岛像一堆堆垃圾坐落在这座敏感城市前面。
“谁知道这城里的情况?”凯利问。
“我们不是要一起走吗?”缪斯问道。“我原以为我们要一起走的。”
“他们把我的支票扣留在事务长办公室里了,”凯利解释说。“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想事务长要替我妥善安排用度呢。”他无可奈何耸耸肩膀。“我可不情愿,我不得不去猎取一个富有的太空情种,好好交个朋友。”他又喝了一口茶;这时凯利注意到其他人沉闷得一声不吭。“噢,得啦,走吧!你们再这样盯着我,我就要把你们从青春期就细心保养好的身体里的一根根骨头都打断。嗨你!”他说的是我。“你不要给我装什么圣洁的呆样,好像你从来没有跟太空情种调情过!”
事情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并不呆,也不傻,”我说着,气得快要发疯了。
渴望,多年的渴望。
鲍笑了笑,打破紧张的气氛。“我说呀,上一回我在伊斯坦布尔——大约一年前我入伍到这个排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正要离开塔克斯姆广场到伊斯蒂勒尔。就在那些廉价电影院的另一头,我们发现了一条两旁簇满鲜花的小路。在我们前头有另外两个太空人。那儿是个市场,再往前是卖鱼的地方,接下去是个院子,摆满橘子、糖果、海刺猬和卷心菜。但是鲜花摆在前面。不管怎么说,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太空人有几分滑稽可笑。我说的不是他们的制服:那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的发型:很好看。我们听见他们讲话才觉得滑稽可笑——那是一男一女,装扮成太空人,想要猎取太空情种!你们想想,竟然对太空情种如此着迷!”
“是呀,”洛说。“我以前也见过。在里约热内卢这号人多的是。”
“我们狠狠揍了那两人一顿,”鲍最后说道,“我们在一条侧街里教训了他们,于是进城去!”
缪斯的茶杯卡嗒一声放在柜台上。“从塔克西姆到伊斯蒂勒尔直到你们进入花街?那你干吗不说那儿是太空情种的聚居地呢,呃?”凯利只要装个笑脸就没事了。但是凯利没有笑容。
“混蛋,”洛说,“谁也用不着告诉我到哪里去看热闹。我一走到街上,太空情种就闻到我来了。我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半路就能认出他们来。这地方除了茶难道就什么也没有吗?到哪儿能弄杯酒喝喝呢?”
鲍咧开嘴笑了。“这是穆斯林国家,记得吗?不过在花街尽头有好几家小酒吧,.绿色的门,大理石柜台,花上大约相当于十五美分的几个里拉,你就能喝上一升啤酒。那儿到处都有这种货摊出售煎得油腻腻的昆虫和猪肠三明治——”
“你是否注意到太空情种怎样才能把它吞食掉?我说的是酒,不是……猪肠。”
由此引发出许多消除火气的故事来。最后我们讲了个太空情种的故事:有个太空人想趁他喝醉的时候偷他口袋里的钱,那人宣布说:“我有两种追求。一是太空人,二是好好打一架……”
但是这些故事只能减轻内心的痛苦,无法医治心灵的创伤。现在连缪斯也知道我们要分离度过这一天了。
雨停了,我们坐渡轮到金角。凯利马上向别人打听怎样去塔克西姆广场和伊斯蒂勒尔,人家指给他一个多尔玛什。我们发现那是一辆出租车,这种出租车只到一个目的地,一路上搭乘一批又一批乘客。车费非常便宜。
洛一路走过阿特图尔克大桥,想看看新市区的景色。鲍决定要搞清多尔玛·鲍奇到底是什么玩艺儿;缪斯发现花十五美分——就是一里拉五十克拉什——就可以到亚洲去,于是缪斯决定到亚洲。
到了桥头,我拐弯穿过混乱的车流,从旧市区电车架空线下灰暗、滴水的墙边走过。有时候叫嚷和欢闹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有时候你得独自一人行走,因为孤独一人太伤人心了。
我走过一条条小街,街上湿漉漉的驴子、湿漉漉的骆驼和带面纱的妇女络绎不绝;我又走过一条条大街,到处是公共汽车、一筐筐垃圾和衣冠楚楚的男人。有些人睁大眼睛盯着太空人;有些人则不然。有些人是否盯着太空人,他们的目光是任何太空人在十六岁从培训学校毕业以后一星期内就能认得出的。我正在公园里散步,见到她注视着我。她见到我看见了就把目光移开。
我从从容容走在湿漉漉的沥青路上。她站在一座空荡荡的小型清真寺的薄壳型屋顶下。我从清真寺前面走过,她走到外面院子里,站在大炮中间。
“对不起,打扰了。”
我停下脚步。
“这里是不是圣艾琳神殿,你知道吗?”她讲的英语自有一种迷人的口音。“我把游览指南放在家里忘记带上了。”
“很遗憾。我也是游客。”
“哦。”她笑了。“我是希腊人。我原以为你是土耳其人呢,你的肤色这么黑。”
“我是美国红皮肤印第安人。”我点点头。她还了一个屈膝礼。
“我明白了。我刚上这里伊斯坦布尔的大学。你穿这身制服,我看出你是”——停了一下,所有的猜测都释然了——“你是太空人。”
我感到不自在。“是的。”我把双手插进口袋里,用靴底来回磨蹭着地面,舌头舔着左侧后面第三颗臼牙——做了一个人不自在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一个太空情种一度对我说过,这种表情叫人兴奋之至。“是的,我是太空人。”我说话太急太大声,她稍稍吓了一跳。
所以,现在是她知我知、我知她知了,我心里想着怎样把这一出普鲁斯特老套路的戏一直唱到底。
“我是土耳其人,”她说。“我不是希腊人。我不是刚刚上大学。我是这里大学的艺术史研究生。这些小小的谎言是用来搪塞陌生人以保护自我的……嗯?有时候我想我的自我太藐小了。”
这是一个计谋。
“你的住处有多远?”我问道,“按土耳其里拉计算现在是什么行情?”
这也是一个计谋。
“我没有钱可以花在你身上。”她拉拉雨衣把臀部裹裹紧。她非常漂亮。“我想在你身上花点钱。”她耸耸肩膀,嫣然一笑。“不过我是……穷学生。不是富有的学生。假如你想转身走开的话,心里丝毫也不会感到为难。不过我会伤心的。”
她呆在路上不走。我想她过一阵子就会出个价。可是她没有开价。
这又是一个计谋。
我在问自己,你要那些臭钱派什么用场?这时从公园高大的柏树里刮来一阵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水面。
“我想那种事真可悲。”她擦掉脸上的雨滴。她的嗓音有些哽咽,有一阵子我过于专注凝望着水上涟漪。“他们要把你培养成太空人,只好改变你的躯体,我想太可悲了。倘若没有改变你的躯体,那么咱们就……倘若太空人的躯体都没有被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你原先是男性还是女性?”
又是一阵雨。我正低头望着地面,小雨滴从我的衣领上淌下来。
“男性,”我说,“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