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之路 (第3卷)-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登于《惊奇》的一篇题为《最后期限》的故事里,克利夫·卡特米尔精确地描述了原子弹:肾是怎样构造的。1945年之后,作家们再也不能把这种炸弹当作科幻小说来描写了,因此在一段为期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设想爆发一场疯狂的全球原子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些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数西奥多·斯特金写的《霹雳与玫瑰》,故事发表于1947年11月号的《惊奇》上。在若干年内,充斥市场的是主流作家有关原子厄运的故事,科幻小说杂志放弃这一题材,因为它再也不那么新奇了。
斯特金(1918-1985)在作家之中可能最有资格描述对美国进行原子弹突然袭击的问题。在海上当了三年机舱清洁工之后,斯特金开始为坎贝尔的《未知》,而后为《惊奇》写作。1939年他在这两种杂志上都发表过故事。他早期发表在《未知》的故事,例如《他穿梭般往来》、《它》、《肖特尔·博普》和《极端自我主义者》为他赢得了幻想作家的名声,但他占优势的作品是科幻小说,例如《微观宇宙的神》、《铬制的头盔》、《打瞌睡的杀手!》和《缪霍的喷气机》。
他在50年代早期给《银河》写了《婴儿三岁》、《孤独的碟形凹地》、《英雄科斯特洛先生》、《老奶奶不编织》和《为了娶蛇发女妖美杜莎》,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和姊妹杂志《冒险》上发表了《柔滑的雨燕》、《绿猴事件》、《姑娘有胆量》、《不太熟悉》和《丧失海洋的人》,通过这些故事他发现了自己的主题、爱心和技巧,形成了细腻的散文笔调,这种散文可以上升为诗歌,也可以下降为暴力。
像布拉德伯里一样,斯特金是出于本能随心所欲写作的短篇小说作冢。十年过去了他才着手写一邵长篇小说(《做梦的宝石》,1950),他最著名的书《不纯粹是人》(1953)当年荣获国际幻想小说奖,该书由两部中篇小说组成,这两部中篇又是围绕第三部中篇小说《婴儿三岁》构思的。短篇小说作家面临严重的问题:短篇故事稿酬不多,除非卖给第一流的畅销杂志(即便在战后,科幻小说杂志最高稿酬每字也只有两美分,直到1950年《银河》把它提高到三四美分)。长篇小说作家比较容易出名,容易赢得一批崇拜者,书也比较容易出版。
斯特金好不容易成功了,尽管他一度想改行,也曾受诱惑写了其他种类的书,例如《我,浪子》(笔名为弗雷德里克·R·尤英)和扩充的长篇小说《海底航行》,然而他的短篇小说大多编入文集,或者汇编成书,例如《没有妖术》(1948)、《E普鲁里伯斯独角兽》(1953)、《回家之路》和《鱼子酱》(二者均为1955)、《不太熟悉》(1958)和其他书籍。他还写了《宇宙洗劫案》(1958)、《维纳斯+X》(1960)和《你的部分血液》(1961)。
最近几年他在好莱坞工作,因此科幻小说作品减少了,但他还是常常重操旧业,因写作《缓慢的雕塑》于1971年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并且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题为《斯特金无灾无病活着》(1970)。
在科幻小说领域,如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体裁特征甚为重要,主要目的是要出版和归类销售(对于零售商和读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价值在于作者赋予作品的独特品格,亦即作者自己所关注的事物,这种关注使得他的作品不“仅仅是”科幻小说。
斯特金对科幻小说最重大的贡献一直是他对风格的关注。其次是他始终认为爱是人类得救的唯一途径,他的故事以多种形式表现了这一主题。他于1953年为一家称为《天空挂钩》的热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重印于戴蒙·奈特的《转折点》),题为《朔望为何这么多?》。“朔望”是“聚集”、“会合”的意思,他写道:“几年来我一直在尽力调查研究爱的问题,包括性爱和非性爱。我通过写作来调查研究爱……因为在我向别人讲述爱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的是什么。”
在《不纯粹是人》一文中,一帮流浪者的完形将个别的才能联合成具有非凡能力的生物。但是在完形能够起作用之前,个别的人必须学会互相信任、互相爱护。斯特金在他的全部小说中似乎在说,人因为未能爱人,因此不是真正的人。
或者可以这么说:只要我们表现出爱心,我们就可能不纯粹是人。
《霹雳与玫瑰》'美' 西奥多·斯特金 著
当皮特·莫萨知道有演出的时候,他转身离开统帅部的布告牌,摸摸长下巴,决定刮刮胡子,尽管演出只是电视直播而已,他将在营房里观看。他还有一个半小时。又找到一点事干干,挺开心的——即便是在八点钟以前刮刮胡子,这种小事干千也不错。星期二,八点钟,老一套。星期三上午人人都说:“昨天晚上斯塔那首《微风与我》唱得怎么样?”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在那次攻击之前,在所有那些人死去之前,在国家灭亡之前。斯塔·安思姆——众望所归,就像克罗斯比,就像杜斯,就像詹妮·林德,就像自由女神铜像。(自由女神是首批挨炸的目标之一,她那美丽的胴体已经挥发殆尽,带有放射性,现在正随着无定向的风四处漂泊,散布到整个地球……)
皮特·莫萨哀叹一声,迫使自己的思路离开被炸毁的女神像飘忽不定的有毒碎片。仇恨压倒一切。仇恨无处不在,就像夜间空中日益增强的蓝光,就像笼罩着基地的紧张气氛。
右方远处响起零零落落的枪声,枪声越来越近。皮特来到外面街上,向一辆停着的卡车走去。有个陆军妇女队员坐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在街拐角,一个身材粗大的人走到十字街口。此公平端着一杆冲锋枪,左右晃荡,就像风标轻轻地摇摆着。他向他们蹒跚走来,枪口搜寻着目标。有人从一座大楼里开火,那人转过身,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胡乱开枪。
“他——瞎了,”皮特·莫萨说道,看见那张破烂的面孔,又补上一句:“他准瞎了。”
警报器发出凄厉的声音。一辆装甲吉普车拐入街道。两支0.5口径的机关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射击声,结束了这一事故。
“可怜的疯小子,”皮特低声说。“这是我今天见到的第四个人了。”他望着陆军妇女队员。她笑盈盈的。“嗨!”
“哈罗,中士。”她一定早就认识他了,因为她既没有抬头,也没有大声说话。“出什么事啦?”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个小子没仗好打,无处可跑,活腻了。你怎么啦?”
“没什么,”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她终于举目望着他。“我说的是这一切。我似乎记不得了。”
“你——呃,这一切可不容易忘掉。咱们遭到攻击了,各地同时遭到攻击。所有大城市都毁了。咱们受到两边夹击,太厉害啦。空气变成放射性物质。咱们全都——”他克制着自己。她不知道。她忘了。无处可逃,她已经逃进自己的内心深处,就在这儿。干吗要告诉她这一切呢?干吗要告诉她人人都将死去呢?干吗要告诉她另一件可耻的事:我们没有反击呢?
但是她没有在听。她仍然望着他,目光游移不定。一只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另一只眼睛稍稍偏离,似乎看着他的太阳穴。她又露出笑容。当他的话渐渐低沉下去的时候,她没有催他说下去。他慢腾腾走开。她没有回头顾盼,只是一直凝望着他原先站立的地方,脸上略带微笑。他转身离去,走得很快,巴不得跑掉。
一个人能熬多久呢?当你在服兵役的时候,他们尽力把你塑造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其他人一个个正在死去,你怎么办?
当最后一个人神志正常死去的时候,他抹掉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前他一直在效法那个人。世态总是使人认定最好要出人头地。他还没有条件走到这一步。然后他把这种想法也抹去了。每当他对自己说还没有条件出人头地的时候,心灵深处就有一个声音问他“怎么没有条件呢?”他似乎从来拿不出一个现成的答案。
一个人能熬多久呢?
他登上军需中心的台阶,走了进去。接待处配电盘旁边空无一人。没关系。信件是用吉普车或者摩托车送来的。当今基地司令部不再坚持人人都得坐班坚守岗位了。吉普车上或者焦虑万分的军队班里每死掉一个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可能就得死掉十个。皮特决定明天下到班里去度过一小段时光,这对他大有俾益。他希望这一回副官不致于在阅兵场的中央放声大哭起来。你可以把思想好好集中在兵器教范上,直到发生那种哭鼻子的事。
他在兵营走廊上偶尔遇见索尼·怀斯弗伦德。这位年轻技术员的圆脸蛋像以往一样兴致勃勃。他一丝不挂,浑身通红,肩膀上披着一条浴巾。
“嗨,索尼。热水很丰盛吗?”
“干吗不呢?”索尼咧开嘴笑着说。皮特也咧开嘴笑了,心里纳闷除了热水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东西,谁还能谈论别的什么劳什子呢。…不消说,热水有的是。军需军官营房里有供应三百人的热水,眼下只剩三十几号人,一些人死了,一些人到山里去了,一些人被禁闭起来,免得他们——
“斯塔·安思姆今晚有演出。”
“没错。星期二晚上。没啥意思,皮特。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场战争——”
“别开玩笑了,”皮特连忙截住他的话。“她在这儿——就在这基地上。”
索尼喜气扬扬。“哟。”他从肩上拉下浴巾,把它围在腰际。“斯塔·安思姆在这里!他们准备在哪里演出?”
“在司令部吧,我想。只是电视直播。你知道眼下禁止公共集会。”
“不错。这也是好事一桩,”索尼说。“在现场肯定有人会垮掉。我才不愿她看见那种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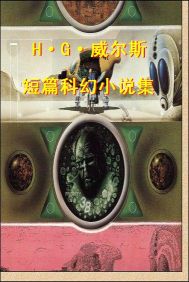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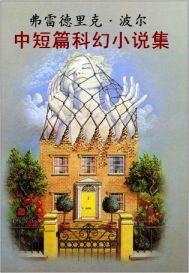
![[综]魔王的升级之路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