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之路 (第3卷)-第1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才会改变每年的元旦。所以现今在卡海德首府厄亨兰是元年春季,我有生命危险,自己却全然不知。
我参加了一次游行。我恰好走在杂音号吹奏手后面,国王前面。天下着雨。
雨云笼罩着阴暗的塔楼,雨水泻落在纵深的街道里,这座黑暗的石头城正在经受风暴的袭击,一条金矿脉慢慢地蜿蜒穿过这个城市。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厄亨兰市的商人、权贵和工匠,一排又一排,穿着华丽的服装,队伍在雨中行进,犹如鱼儿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着。他们脸上流露出热切和平静的神情。他们步伐散乱,没有齐步走。这是一支没有士兵的游行队伍,连假冒的士兵也没有。
紧接着到来的是领主、市长和各方代表,卡海德各领地和联合领地派出一人、五人、四五十人或者四百人,这支装饰华丽的’庞大队伍和着音乐的节奏款款走来,吹奏的乐器有铜号、一块块空心骨头和木头以及发出枯燥、清亮节奏的电动长笛。大领地各式各样的旗帜颜色斑斓,在风雨中混杂在一起,与路上迎风招展的黄色三角旗争相斗艳,每一队演奏的各种音乐嘈嘈杂杂互不协调,交织成多种旋律,在纵深的石头建筑街道里回荡。
接着走来一队玩杂耍的人,手拿闪闪发光的金球,他们把球高高抛起,球闪着金光飞起落下,他们接住,再抛起,金球纷飞,如同一片灿烂的喷泉。顷刻间仿佛他们真的抓到了阳光,金球像玻璃一样光芒四射;太阳冲破乌云出来了。
接着是身穿黄色服装的四十个男子,吹奏着杂音号。杂音号只在国王面前吹奏,发出一种古怪、忧郁的吼声。他们四十人一起吹奏,声音震耳欲聋,震得你神经错乱,震得厄亨兰塔楼摇摇欲坠,震得乱云洒下最后一阵雨。假如这就是皇家音乐的话,难怪卡海德诸王个个都是疯子。
再接下来是皇亲国戚、卫队、城市和法庭公务人员、高官显贵、各界代表、参议员、大臣、大使、王国贵族,他们步伐散乱,不成队形,然而一个个神气十足,摆着架子昂首挺胸行进着;他们当中有阿加文国王十五世,穿着白色短袖束腰长外衣和马裤,打着橘黄色皮护腿,头戴一顶黄色尖帽子。他戴着一个金戒指,这是他唯一的装饰品.也是权力的象征。在这一群人后面有八十个体魄强健的人抬着皇家轿子,轿子上镶满密密麻麻的黄宝石,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哪一个国王乘坐过这顶轿子,它只是久远时代礼仪上的遗物而已。轿子旁边走着八名卫兵,手持“劫掠之枪”,这也是历史上较野蛮时期的遗留物,但枪支不是空的,里面装填着柔软的铁弹丸。死神走在国王后面。死神后面走来了工匠学校、大学、职业学校和王族的学生,排成长蛇阵,都是些身穿白、红、金、绿各色服装的孩子和年轻人;殿后的是几辆缓缓行进的黑色轿车。
皇亲国戚(鄙人跻身其间)聚集在未竣工的河口拱桥旁边用新木材搭建的平台上。这次游行就是为了庆祝拱桥的最后落成,这座桥将使新路和河港连为一体,是个历时五年的大工程,包括疏浚河道、架设桥梁和修路,这项工程的完成将使阿加文十五世的统治以卓越的功勋载入史册。我们穿着潮湿又笨重的华丽服装,全都簇拥着挤在平台上。雨停了,太阳照在我们身上,恒冬的太阳灿烂辉煌、光芒万丈、说变就变。我向左边的人说:“很热。太热了。”
我左边的人是个又矮又胖的黑皮肤卡海德人,有着柔滑而浓密的头发,身穿一件滚着金边的笨重绿色皮革大长袍、一件肥大的白衬衫、厚实的马裤,挂着一条沉重的银环项链,每环足有巴掌那么大——此公大汗淋漓,他回答说:“是很热。”
当我们拥挤在平台上时,我们四周是密密层层的市民,一张张像褐色鹅卵石的面孔翘望着我们,千万双眼睛像云母一般闪烁着光彩。
此刻国王登上了原木搭成的跳板,跳板从平台通到拱桥顶端,遥相呼应的两个桥墩高高矗立在王冠、码头和河流之上。国王往上走,这时民众之中群情激昂,齐声呼喊着:“阿加文!”
他没有反应。民众也不需要他做出反应。杂音号吹奏手胡乱吹了一阵,声音如雷,立刻停了下来。鸦雀无声。太阳照射着城市、河流、民众和国王。下面的泥石匠已经开动一台电动绞车,当国王越登越高时,拱桥的拱顶石用吊链吊起,经过国王身边,继续吊高,安放下来,尽管是成吨重的大石块,却几乎无声无息地套进两个桥墩之间的缺口里,使得两个桥墩连成一体,成为一座拱桥。一个泥石匠手拿泥刀和圆桶,站在脚手架上等待着国王;所有其他工匠顺着绳梯爬下去,活像一大群跳蚤。国王和泥石匠跪下,高高地介于河流和太阳之间,跪在那块跳板上。国王接过泥刀,开始用灰泥涂抹拱顶石四周长长的接缝。他不用泥刀把灰泥抹平,将泥刀还给了泥石匠,但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干了起来。他用的水泥是桃红色的,不同于其它灰泥涂料的颜色。
观看这位蜂王忙碌五至十分钟以后,我问左边的人:“你们的拱顶石都是用红色水泥加固的吧?”
因为旧桥的每块拱顶石四周都一清二楚是这一种颜色,旧桥造型又高又美,横跨在拱桥上游的河段上。
那男人揩揩黑色额头上的汗水——既然说了他和他的,我得说那是个男人——那男人回答说:“很久以前,拱顶石总是用磨碎的骨粉和血混合成的灰泥加固的。人的骨,人的血。你知道,没有血作粘结剂的话,拱桥会倒塌的。当今我们用的是动物的血。”
他经常这样讲话,坦率又谨慎,令人啼笑皆非,好像总意识到我用外星人的标准进行观察和判断:在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种族中又身居如此高的地位,他的这种意识堪称奇特。他是这个国家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我吃不准他的职位相当于历史上哪一号人物,可能是大臣,或者首相,或者参议员;他的职位用卡海德的话来说,意思是国王的耳朵。他是一个领地的领主和王国的贵族,重大事件的提议人。他名叫西伦·哈思·伦厄·埃斯特拉文。
国王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泥石匠活儿,我很高兴;但是他在拱桥隆起的圆弧下面走过蜘蛛网似的厚木板,开始往拱顶石另一边接缝里涂抹灰泥,那块石头毕竟有两边嘛。
在卡海德,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他们决不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粘液质的人民,然而他们十分顽固,他们十分执着,他们在接缝里涂好了灰泥。
塞斯河河堤上的人群乐于观看国王干活儿,我却感到厌烦,感到燥热。在恒冬上面我以前从未受过这么热的罪,以后也决不会再受这种罪;我无法热心观看这种隆重的大场面。
我穿的乃是冰河时代的衣服,不是用来抵挡阳光的,一层又一层的衣服,有针织的植物纤维,有人造纤维,有皮毛,有皮革,里里外外形成一套笨重的御寒盔甲,我现在就像一片小萝卜叶子那样失水枯萎着。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看着平台周围的人和继续向平台围拢来的其他游行人员,他们仍然扛着领地和部族的旗子,旗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
我懒洋洋地问埃斯特拉文,这是什么旗子,那是什么旗子,另一面又是什么旗子。
尽管有好几百面旗子,但凡是我问到的每一面旗子他都说得出一个名堂,有些是皮尔灵风暴边境和克姆兰偏远领地、家族和小部落的旗帜。
“我自己就是克姆兰人,”我心里正在钦佩他的见识,他说道。“不管怎么说,了解各个领地是我份内的事。领地组成卡海德。统治这块国土就是统治它的领主们。我不是说领主们一向服从统治。你是否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语:卡海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家庭?”
我没听说过,我怀疑这话是埃斯特拉文瞎编出来的,他就是那一种人。
就在这时,埃斯特拉文领导的“京理米”,即上议院或谓国会的一个成员一路推搡着挤到他身边,开始跟他讲话。此公乃是国王的表弟彭默·哈治·伦厄·泰博。他跟埃斯特拉文讲话的声音很小,姿态隐隐约约有几分傲慢,脸上频频露出笑容。埃斯特拉文汗流浃背,如同在太阳下暴晒的冰块,却仍然像冰块一样圆滑而冰冷,他大声回答泰博咕咕哝哝的话语,语气里充满客套式的礼貌,使对方显得像个大傻瓜。我一边观看国王继续涂抹灰泥一边听着他俩的谈话,但是除了听出泰博和埃斯特拉文之间的敌意之外,我什么也没听懂。反正此事与我无关,我只是对统治着一个国家的这些人的行为举止感兴趣而已,从守旧的意义上说,他们毕竟掌握着一千万人民的命运。权力在伊库曼人的生活方式中已经变得非常阴险而且非常复杂,因此只有心术阴险的人能够耍弄权力;在这里权力还是有限的,还是看得出的。例如,在埃斯特拉文身上,人们觉得此人的权力是他名声的进一步扩大;他不能做出一个空姿态或者说出一句没有人听的话。他懂得这一点,这使他变得比大多数人更加看重现实:人生的安定,殷实的生活,人的显贵。一事成功万事顺利。我不信赖埃斯特拉文,他的动机一向十分暧昧;我不喜欢他;然而我感觉得到他的权力并对他的权力作出反应,就像我感觉得到太阳的热量并对它作出反应一样确凿无疑。
我正想着这档子事,这个世界的太阳被重新聚拢的乌云所遮蔽,日光暗淡下来,顷刻间上游下起一阵稀稀落落的大雨,雨水淋着河堤上的人群,天空转暗。当国王走下跳板的时候,最后一道闪电照亮大地,国王的白色身影和大拱桥衬托着乌云密布的南天清晰地闪现出来,显得特别生动和壮观。乌云聚拢。一阵冷风刮来,呼啸着扫过港口~宫廷大街,河水发浑,河堤上的树木颤抖着。游行结束了。半小时以后天下起了雪。
当国王的轿车沿着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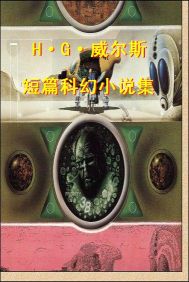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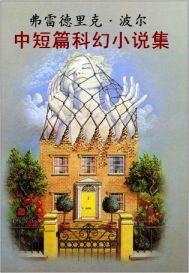
![[综]魔王的升级之路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