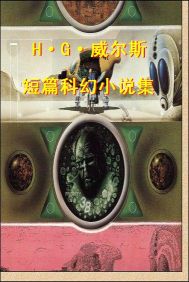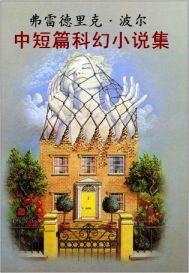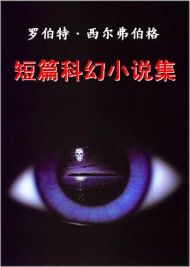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九辑)-第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把这位已故教授的某些思想加以发挥,我在1950年发表了论文,其中驳斥了希伍德关于在平面地图上着色必需有五种颜色的“证明”。①按照拓朴学家的普遍看法,平面或球面的着色有四种颜色就够了。
在论文问世后不久,我偶然在学校的《四角形》俱乐部和阿尔玛·布什共进早餐。阿尔玛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教授,当然,她肯定也是全校最美丽的女性。
阿尔玛刚从一个小岛考察归来,那海岛离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海岸有几百英里,她率领了一批学生对岛上五个部落的风俗习惯进行研究。
“全岛分成五个地区,”阿尔玛告诉我,一面把香烟插进她那长长的黑色烟嘴,“它们全都互相接壤,这对理解当地的风俗很重要,具有公共边界使各部落都保持了某些统一的文化。你怎么啦,马丁?你脸色干嘛如此吃惊?”
我站起身,把送到嘴边的叉子慢慢放圆桌上。
“因为,你讲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根本不可能。”
阿尔玛感到不大自在。
“为什么不可能?”
“五个部落,又都有着公共边界:这和著名的四色问题是矛盾的。”
“和什么有矛盾?”
“和四色问题,”我重复道,“拓朴学里有这个题目,尽管谁也没能证明或否定它,但谁都不怀疑它的正确性。”
我拿起匙柄在台布上画了起来,打算给阿尔玛解释清楚。阿尔玛很快就掌握了要点。
“也许,岛上的部落另有一种数学呢?”她发表见解,由于烟雾而眯起了眼睛。
我摇了摇头。
“亲爱的,数学对于所有文化都是唯一的,二乘以二就是在非洲也还是等于四。如果岛屿真的如你所说分成五个地区,而每个地区又都和另外四个地区具有公共边界,那我真要相信你那些岛民的数学天才了。你没有岛上的地图吗?”
阿尔玛否定地摇摇头。
“也许,你跟我们走上一次?”
她建议说,弹了下烟嘴,“我还得在岛上耽误个把月,有些资料在发表前得再核对一下。这段时间你可以把岛上的地图搞出来。如果我对你所讲的话被推翻了,你的一切费用就都由我来报销如何?”
我何乐而不为?好在暑假已经开始,这次旅行看来非同寻常又那么诱人,我同意了。
到达该岛的第二天,阿尔玛介绍我和一个岛民叫阿古兹的相识,阿古兹是岛上的希依库族人,阿尔玛和他讲好陪我们一齐徒步走遍全岛,好在岛并不大,面积不超过25平方英里,早点出发的话,傍晚时分就能走完了。我随身带上拍纸薄和铅笔盒,以便勾画出哪怕是粗略的五个地区的轮廓。
我们首先拜访的是希依库族,我们的营地就设置在他们这里。
在拍纸薄的首页我画了个圆并涂上蓝色,其实希依库族人所占地区的准确形状我并不清楚,但对我来说,有个大概的样子就可以了。当我们朝西走去时,发现到了沃尔费济族的领土,于是我又在蓝圆的左面画上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并涂上绿色。
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密草丛树,我们来到一条静静的小河岸边,由原木扎成的筏子隐约露出在岸边肥沃的河泥之上。阿古兹把木筏推到水中爬上去,用长长的竹篙拉了起来。我们趟着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带也上了木筏,阿古兹就用竹筒左转右折地使筏子顺着弯曲的河道向下游驶去。
过了一段时间阿古兹招呼说,我们已到了格泽洛莫族的地盘。它位于沃尔费济人的北方,我从拍纸薄上赶走一只大晴蜒,并在所谓的地图上标上个红色斑点,它位于绿块的上面。
在格泽洛莫人的领土里又驶行半英里左右,阿古兹把筏子靠向岸边,我们上了陆地.然后在山坡上奋力跋涉,穿越了高可半人的草丛——我们已站在格泽洛莫人的村子外面。
顺利地绕过了村子,我们转向东南方向。又走了一英里光景,阿古兹指着远处一排种植整齐的棕桐树说,那就是格泽洛莫族和希依库族的界树,我掏出拍纸薄,把红斑继续扩伸到蓝圆之外。
刚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别博卢普族的居民点。就我所想象的那样,把这块领地涂成了紫色,使它延伸到南方,然后又到西边,把蓝圆的下方都包上了,最后还联上了绿色,我把草图递给了阿尔玛。
“瞧,蓝色地区的四面都被另外三种颜色包没了,这样第五个地区是不可能和它们全都接壤的。”
阿尔玛把地图给阿古兹看,她俩指手划脚地交谈了一阵子。
“阿古兹说,他不知道从天上来看他们岛子是个什么样子,但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是弄错了。”我瞧了下阿古兹,他面部肌肉纹丝不动,但我有些不快:他内心在想我是个白痴。
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块领土实在难以描述,它根本就毫无特色可言。这第五个部族没有酋长,不知道什么劳动分工和亲属关系,也没有在出生、结婚或死亡时的成套仪式,部族里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传说的风俗习惯,更有甚者,他们连族名都没有。
第五块地区我涂的是黄色,我们走遍了它和绿色、红色及紫色地区的分界地段,当阿古兹最后指着小河对岸说,打那儿开始就是希依库地区(蓝色地区)时,我混身简直好象起了鸡皮疙瘩。
“决无可能!”我嚷道,“除非我们在某个地方已经穿越过别人领土了!”
阿尔玛把我的话译给了阿古兹,他直摇晃脑袋瓜子。
当然,我坚信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庇漏:可能某块领土是由两个单块组成的;也可能是阿古兹指错了交界线,肯定有问题!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和阿尔玛爆发了争论,她断定说我输了,所以理所当然要自己掏腰包付旅费。
我用手帕擦了下额角,要是能作出五个地区的精确地图该有多好!不过这需要进行地形测量,而我们连一件仪器设备也没有。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你认为怎样?”我问阿尔玛,“在蒙罗维亚能租到象喷雾器那种玩艺吗?”
阿尔玛在香烟雾中眯紧双眼,她说按她的估镀此事完全可能。
“如果我们能搞到喷雾器,”我继续说,“我们就可以在每块区域里都喷上一些相应的彩色斑块,再通过空中彩色照相就能使每块领土都异彩毕现了。”
阿尔玛认为我的办法很棒,她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份全岛地图,而我的建议将使这个任务以最快速度实现。
“颜料可以算在我的帐下。”她慷慨赞助。
这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始所讲的那一幕情景,从建筑行业的承包商那儿,我们租来了一打喷洒涂料的喷枪,又买了共二万加仑最便宜的各色涂料。回到岛上,毫不费劲地招募到由希依库族孩子组成的工作队,并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喷枪。
阿古兹被指定为队长,给每个部落的领土都规定了一种颜色,就象我在《草图》中所用的那样。当然,要把全部土地都喷色,花销也太大了,我们决定每隔一百英尺的距离才喷上一个直径为十英尺的斑点。从飞机上看下面就象是缀满了豌豆花点似的,分界线将清晰可辨。
每次我都跟着工作队出去,以便监督全过程,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在前四块领土之间都相互存在着公共边界是毋庸置疑的:每一块都有某些边界地段和其他颜色的领土毗连。
关键在于那第五种颜色。
从第十二个工作日开始喷涂黄色,而黄色地区已经和红色、绿色以及紫色地区接上了头,我们离蓝色地区越来越近,我的神经也紧张到了极点。
工作队穿过林边的灌木树丛慢慢地移动,落日的余辉在大地上留下长长的树影。被涂料玷污了美丽羽毛的飞禽纷纷四散飞避,一条溅上黄点的棕色小蛇咝咝地爬向幽暗的藏身处,我猛然抓住了阿尔玛的肩头。
“该诅咒的默比乌斯幽灵!”我嘶哑地说,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一阵狂跳,“我在这儿看到蓝色的斑点啦!”
阿尔玛美丽的灰眼睛透出胜利的闪光:“那么倒底谁是正确的?”
我找个大树墩坐下来,擦一下淌满全脸的汗珠,头痛欲裂,太阳穴也怦然作动。透过单调无休止的虫鸣声,远处传来别博卢普人的隆隆鼓声,阿古兹也站着等待待下一步的指示。
我实在六神无主,严格说,五个地区怎么也不可能全都互相接壤的占我知道四色问题在国家数不超过35时已经得到证明,但万一这个证明藏有某种错误呢?如果小岛果真推翻了四色问题的论断,那我这个发现将是拓朴学的伟大转折点!
几天后,当定期班机从蒙罗维亚飞来后,我们商定对全岛作空中照相,可惜飞机的座舱大小,只够摄影师带着照像机去飞行。等像片拍完后,驾驶员才让摄影师下来,载上我俯瞰这座五色岛屿。
我神经质地注视飞机缓缓地在上空划了个圈子,然后降落下来,滑行一段以后,飞机停住了。摄影师跳了下来,我急忙奔上前去,打算取而代之,但被那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非洲驾驶员拒绝了。
“摄影占用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多,”他斩钉截铁地说,“半小时后我得返回蒙罗维亚,真遗憾,我一星期后再来带您兜风。”
无论我怎么请求或哀恳都无济于事。当飞机飞走后,我转向摄影师:“从上空看全岛究竟如何?”
“不好对您说,各种颜色交织得太离奇古怪,我本打算勾画张草图,但因过于复杂而放弃。”
我又追问是否有的地区由某些孤立的,被别的颜色所围成的小块所组成时,摄影师否定了这一点:“所有的领土都各自连成一块,而且还都通向海岸。”
“嗯,很有趣。”我嘟哝着,突然一个念头又彻底打垮了我,这使我敲打自己的脑瓜子并呻吟起来。
阿尔玛以为我出事了,朝我脸上泼了凉水,我坐在地上,双手捧头,想哪怕能减轻一些阵痛也好啊。
到底这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