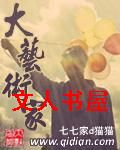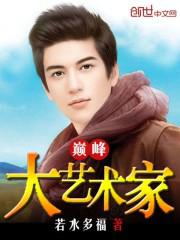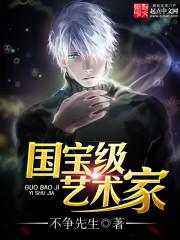大艺术家-第12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类的思想,将格雷诺耶放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就如同他的缺失气味一般,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存在,而这种束缚对于格雷诺耶来说,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他用着自己的执着和单纯,华丽地将一切都碾成了碎片。的确,那些消失的生命代表了罪恶,但是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格雷诺耶却在这一个个消失的生命里,试图寻找着自己的存在,可悲的是,他永远都找不到了。
他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天使,他用最灿烂而绚丽的方式绽放着他的生命,因为孤独而无限绚丽、因为执着而无限纯粹、因为短暂而无限辉煌的生命,宛若那瞬间绽放的烟花,在漆黑的夜空之中肆无忌惮地释放着所有的艳丽,然后划过天际,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祈祷着,在历史与文学的广袤沃土上,能够给这样奇异、自由、怪诞的灵魂留下一小片属于它的土壤,让它能够无视法律与伦理,自由自在地翱翔。”
“展映”的评论如诗如画,让人用如同电影般诗意的目光重新审视这部电影。这是一种新颖却专业,但是又值得深思的视角,成为了“香水”支持者阵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站在这些媒体的对立面,也有一群嘶吼咆哮着的媒体,这群媒体的力量丝毫不逊于赞美者,他们竭尽自己的所能,将人们的思想拉回原本的轨道,用尽所有的词汇,将“香水”这部电影推向道德的绞刑架,宣判这部作品的堕落,从而避免道德的沦丧。
“首映”这一次也出现在了戛纳电影节之上,三大欧洲电影节之中戛纳是对好莱坞最友好的电影节,美国媒体在戛纳的身影也是除了多伦多之外最多的,所以“首映”第一时间撰写了影评也是预料之中的。这一次,艾略特·卡特终于可以畅所欲言、酣畅淋漓地发泄自己对于埃文·贝尔的不满了!不仅因为他有许多同盟,也因为“香水”这部电影给予了他足够的机会。
“道德的沦丧”,这成为了艾略特·卡特的影评标题,再搭配上零分的评价,如此重的评语和打分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首映”对于“香水”这部电影的立场了,不仅仅是指责,更是严重的批判。
“当看完‘香水’的时候,我已感觉到出离的愤怒,埃文·贝尔借用着文艺这把双刃剑,如此赤果果地抹杀了真理,如此赤果果地赞颂罪恶,这已经超出了道德的底线。如果一部文艺作品没有一个真理的立场,有的只是模糊的是非观,就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埃文·贝尔镜头底下的世界美不胜收,细腻的叙述、漂亮的画面、唯美的配乐、影帝级别的表演,可惜的是,电影里将人的欲望、人的自私、人的狂妄放到了最高的位置,它对人的罪恶进行朝拜,它没有找到真正的美好,自身就是一个迷失,更糟糕的是,这种迷失还会对于观众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观众对于人性的矛盾、反思,将会走向一个可怕的极端。
这似乎已经成为所谓文艺作品或者说哲学作品的一种惯例了,模糊天使和魔鬼之间的界线,从而来解读存在主义。电影最后广场上行刑的时刻,主教对着一个连环凶手高呼天使,众人屈服于自己的欲望,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格雷诺耶的天赋魅力所折服,随后又折射到最原始而无度的本能之中,这完全是将道德底线弃之不顾的一种做法。影片借用格雷诺耶对气味的天赋,将他的所作所为归咎为一种最纯粹的追逐,以此淡化他所犯下的罪恶,但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如果人人都屈服于自己的欲望,纯粹地追逐着自己的想法,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被罪恶和欲念而占据。
我眼中的格雷诺耶,只是一个无爱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变性人,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他通过掠夺他人的生命而满足自己的理想,除了极度的自我为中心之外,我找不出任何正面的词汇。
我憎恨那些打着信仰名号而为非作歹的人,我憎恨那些披着文明艺术皮囊而破坏道德底线的人,我憎恨那些利用所谓哲学辩证而误导世人的人。香水,一个很棒的命题。无数的鲜花被碾碎提炼萃取,最终获得一滴传世的芳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对鲜花奉献的赞美,而不是赞美那些碾碎鲜花的恶魔!”
艾略特·卡特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遣词造句,竭尽所能表达了对“香水”这部电影的厌恶,他甚至不惜以“零分”这样的评价将“香水”送上的断头台。而这一次,站在艾略特·卡特身后的,是十分庞大的支持者,比当初的“断背山”可要多得多。
严格说来,“香水”上映之后,毁誉参半是最好的评价,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这部电影十分精彩,而百分之五十的人则认为埃文·贝尔将一个恶魔精美包装,是十恶不赦的。所以,以“视与听”为首的赞成派,以“首映”为首的反对派,几乎展开了刺刀见血的搏斗,让“香水”这部电影从首映开始就沦陷在了无止境的争论之中。
第1328章 天使魔鬼
在那喧闹震天、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为“香水”唱了赞歌,并且以深刻而专业的视角,为这个议题下了最后的结论,并且将电影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本在全球电影专业杂志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杂志认为,“埃文完美地完成了对聚斯金德原著小说的艰难改编,这轻松地让他成功跻身为顶级导演的行列”为埃文·贝尔的赞美之声吹响了号角。
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洛狄忒在输给了斯巴达的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后,她在特洛伊王子帕丽斯的心中埋下了欲念,令他听不到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愤怒的吼叫,也忘却决斗失败的耻辱,沉浸在斯巴达的王后海伦那金灿灿的甜美欲望之中。最终引发了特洛伊十年战争。
法国作家萨德侯爵备受争议,他的一生有二十七年都在监狱之中度过,为他的惊世骇俗、为他的“性疯狂”付出代价。他用一根轻巧的鹅毛笔撩拨了全世界的欲望之火,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迫使人们直视自己面对性的尴尬与癫狂。
神话之中的女神,现实中存在的天才,他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创造出崭新的故事,不管用什么手段,他们让人们变成扑火的飞蛾,化为灰烬也在所不惜,甚至还会对那让他们粉身碎骨的灯火感恩戴德。往往,这样的人物出场时,总是伴随着圣洁的颂歌和美好的鲜花,让全世界都为之赞叹。
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也是这样一个天才,在嗅觉方面的天才,他所构建的气味王国也应该用盛大的狂欢来迎接他的驾临。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在弥漫着各种臭气的巴黎出生了,同时伴随而来的不仅有死鱼尸体的腥臭,还有他母亲对他弃之如履,他的一生都在被遗弃之中度过,还有对于身边所有人无与伦比的诅咒。他的诞生带来的不是新生的希望,而是对于身边之人无止境的诅咒,他的母亲被以杀婴罪处死,他的乳母惨死于马车的撞击中,抚养他的加拉尔夫人被抢劫之人割喉而死,皮革厂的主人烂醉如泥淹死在了塞纳河中,他的香水师傅则在沉睡中被残垣断壁掩埋在了湍急的河水里……
无论是外表还是言行,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都不像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天才,他没有围绕在阿芙洛狄忒身边的鲜花和光环,他也没有萨德侯爵妙笔生花的天赋和才思,但是他们同样具备了向人们内心散播恐惧和希望、爱情和痴狂的能力。
1791年,萨德侯爵发表了“瑞斯丁娜的不幸”讲述了主人公瑞斯丁娜所代表的美德,却一再沦为恶性的牺牲品,在一次又一次的阴谋和诬陷之中无所遁形,成为种种淫荡行为的工具,受尽了折磨和蹂躏。1801年,萨德侯爵因为这本书第六次被关进了监狱,他嘲笑那些审判他的人是“因为被揭发而发出的呻吟”,那些人是虚伪的,怀着“从未想到有人如此了解他们”的恐惧将他扔进监狱。这一次,萨德侯爵没有能够再走出来,1814年他死在了疯人院里。在两百年后的今天,萨德伯爵则成为了色情和哲学书籍历史上不可取代的一个存在。
萨德侯爵用他的鹅毛笔揭露了世人对于“性”的渴望和惧怕,所以他被收押,并且被冠以疯子的名号。同样的,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也具备了这种能力,只是他的工具是香水,足以让掌控全世界的香水,他用一滴香水勾起了人们最原始最根本的欲望,然后所有人都冲破了道德最后的底线,单纯地被赤果果的欲望控制,然后吞没。
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无疑是气味方面的天才,埃文·贝尔在电影之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呈现出他古怪的天赋,气味成为了接触认识这个世界的唯一手段。但是同时,他自身缺乏气味却让他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不被这个世界认同和接受,所以他只能孤单寂寞地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个恶臭腐烂的世界继续糟糕下去。
山顶的七年生活让他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存在”,这种恐慌几乎要将他吞没,他的天赋、他的能力、他的身体、他的意识,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决定要寻求自己的存在,他需要一个媒介一个方法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而香水,则成为了他的手段。
当他发现自己能够通过气味掌控他人的时候,他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发现自己具备了上帝统治人类的能力,那种俯瞰人类的畅快感让他逐渐迷失在了气味的世界里。对于他来说,杀死二十五名少女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犯罪的过程,而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他只是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他那个最纯粹最简单也是最丰富的气味世界里,继续坐在他的王位上,掌控着世界的运行。
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任何一个空间里,即使是国王,也没有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他必须付出代价。当然,审判并不一定是送往绞刑架,还可以是精神上的判决与控诉。
所以,当他完成了人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