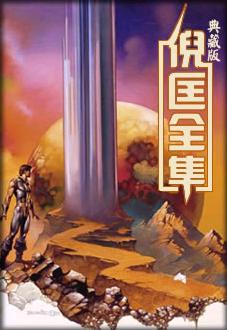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这么回事。”肖莎娜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我甚至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呢?跟孩子一起等着你?我什么也不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嫁了一个士兵。这就是我经常对自己说的话。
“但不是这么回事。我宁愿去扫地。他们没有强迫你去什么地方。”
“好吧,看看再说吧,”阿弗纳说,“开车吧。”
肖莎娜看着他。“我是认真的,”她说。“你还不了解我。”把车从路边开走了。
大约十天过去了,阿弗纳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消息。他自己也没有去问。除了回以色列之外,他甚至不知道跟谁联系,从哪里问起。过去,他总是会有一条指定的信息沟通渠道: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保险箱,某个站的站长。而现在只有特拉维夫的伊弗里姆。给伊弗里姆打电话也没有用,除了说自己屈服了之外没别的可说。他不想给他打电话。
第一个月的房租已经付了,他们搬进了那套新公寓。他们在以前的那栋房子前贴了搬迁通知。新地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他们用的还是以前的电话号码。
他们搬家之后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了。是纽约以色列领事馆的保安打来的。
“这里有你一封信,”那个人说。“你要来这里看一下。”
“难道你寄一下不行吗?”阿弗纳问道。
“不行。信必须留在这里。你来这里看一下就行了。”
也许斯蒂夫是对的,也许是一张支票。第二天早上,阿弗纳乘地铁去曼哈顿。
不是支票。是一份一页纸的文件,很显然是装在外交文件袋中跟其他邮件一起寄来的。文件上说,虽然给阿弗纳规定了回以色列的日期(阿弗纳立即对那个保安说,这是他妈的撒谎),但阿弗纳没有回来。文件继续写道,鉴于此,他们断定,阿弗纳系自动辞职(文件上没有说辞去什么),这样辞职实际上违反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再把钱给阿弗纳,但是他们祝他好运,然后盖章,签名。签名的人是人事处的,认不出来是谁。
阿弗纳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那个保安伸出手,从阿弗纳手中接过文件,把一个登记本推给他。“在这里签字,”他说。“你已经看过了。”
“你什么意思?”阿弗纳问道。“我需要一份复印件。”
“没有复印件。”那个人说。“你已经看过了,在这里签字,我也要签字确认。”
“我没有看。”阿弗纳气愤地说。
“快点,”那个保安说,“别让我得心脏病,这是我的工作。在这条线上签字。”
“休想我签。”阿弗纳说。那个保安没有动。“无论如何,我要谢谢你。”阿弗纳说完,走出了领事馆。
他朝家里走去。那些钱永远没有了。奇怪的是,他感到踏实了。他并不关心这十万块。他做这一切就是为那十万块?如果是为了钱的话,一百万他也不会干。他们没有给他出这个价——或者出任何价。他是自愿的。他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总理和老板让他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任务。当时,他早年崇拜的英雄沙龙大将军也在场,他对阿弗纳说:我希望他们让我去。所以他说了“愿意”。他从来没有向他们要过十万块。他什么也没向他们要。
是伊弗里姆告诉他这个买卖是怎么样的。他也告诉过卡尔、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他对他们说:“不管你在瑞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看看你的账户,你会看见它在不断增加。”伊弗里姆就是这样说的。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问他。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即使到了这一步,也不是钱的问题。是的,让肖莎娜拥有那套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是蛮好的,把那套丹麦厨具和制冰机送给她时,看着她的脸他会非常快乐。是的,他在欧奇大道上盯着橱窗看了几个小时。是的,他曾经还梦见过一次。但是,没关系。他要这些钱的目的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留在美国,去澳大利亚或欧洲,不必做琐碎的工作来养活肖莎娜和孩子,不必在南美或者别的地方追逐恐怖分子。这就是十万块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的。既然他打算放弃不干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容易还是艰难,他和肖莎娜都主意已定,有没有那些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钱,现在也没有钱。没问题。否则的话,它会让伊弗里姆这样的加里西亚人认为,他可以用钱这根线来把阿弗纳像一个木偶似的拉来拉去。
只是有一个问题。
证件的问题。
这么久以来,阿弗纳到处跑用的都是假证件——不是“穆萨德”提供的,就是用“穆萨德”的钱买的,再不就是在执行任务期间汉斯做的——他一想到要用合法的证件,历经无穷无尽、冗长麻烦的官僚程序,就觉得不是滋味。没有外交公务护照的庇护,在限额、工作许可和绿卡的现实世界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弗纳以前到处跑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气氛非常凄凉。
因为阿弗纳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就不能找工作。然而肖莎娜银行存折上的两百块钱,即使在1975年的夏天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必须挣点钱。阿弗纳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别无选择。他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最低等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
他从来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对一个机会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是他无权正式得到的——为了能住在美国——在条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暂时也会去做。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的时候,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样的活他可以干一辈子。
在经历了巴黎、伦敦和罗马的一连串事件之后,经历了一个虚构的乘坐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动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结束了,连谈都不能谈。在这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那辆日本车关掉灯,呼啸着开走了。好像是意识到要掉


![[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106.jpg)